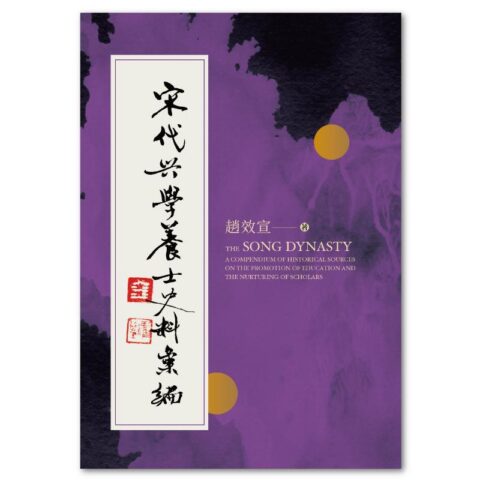青藏高原東緣「民族走廊」因其間民族與文化複雜,被認為是解答中國民族歷史之謎的關鍵。本書以民族走廊上一關鍵民族─羌族,來說明漢、藏與西南氐羌系民族「邊緣」的形成過程。本書首先呈現當代羌族在社會、文化各方面居於漢藏之間的駁雜特性,然後說明造成此「羌在漢藏之間」現象的歷史與文化過程。此歷史過程涉及華夏以「羌」為其西方族群邊緣的宏觀歷史變遷過程,以及許多邊緣人群爭論、建構與遺忘「歷史」並改變其歷史心性之微觀過程。此文化過程涉及─民族走廊上諸人群在中國、吐蕃與近代西方殖民帝國之多重政治文化影響下,透過各種文化表徵相互歧視、誇耀與模仿而成為華夏、吐蕃、以色列人後裔,以及「有共同語言文化的羌族」之過程。藉此,本書對羌族以及中國民族之起源與形成,提出一超乎「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的新詮釋。
作者:王明珂
王明珂,1952年生於台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1992)。現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範圍是中國民族─羌族與中國西南民族,北方遊牧社會之歷史與人類學研究;研究主旨在於人類生態,社會認同與區分,及相關之歷史記憶與文化表徵等問題。1994年以來,多次到川西羌族地區進行田野研究。曾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與東吳大學等校教授歷史與人類學相關課程。
目次
序《羌在漢藏之間》 i
謝詞 ix
前言 xi
文本與田野說明 xxv
社會篇 1
導言 2
第一章 地理環境與人群 5
各行政區簡介 8
語言、體質外貌與文化表徵:誰是羌族? 12
第二章 村寨與城鎮生活 17
村寨聚落 18
村寨中的經濟生活 20
城鎮、街市與鄉上 27
鄰近城鎮:松潘、馬爾康、灌縣與成都 31
第三章 族群認同與區分 35
婚姻與家庭 36
家族 39
村寨與其守護神 46
「羊腦殼」與「牛腦殼」 55
「爾瑪」、「漢人」與「蠻子」 62
「爾瑪」與羌族 77
「一截罵一截」的族群體系 86
第四章 結構下的情感與行為 93
村寨生活中的「我族」與「他族」 94
村寨中的鄰人與女人 97
社會規範、污穢與代罪羔羊 105
岷江上游村寨中的毒藥貓 108
女性與貓:區分的破壞者 114
「內部毒藥貓」與「外在毒藥貓」 121
無毒不成寨 125
經驗、歷史與神話 127
「現在毒藥貓少多了」 134
歷史篇 137
導言 138
第五章 羌族史:典範與解構典範 145
典範的羌族史 145
近代國族主義下之民族與中華民族 151
典範羌族史的形成過程 159
第六章 羌族史的再建構:華夏邊緣觀點 171
商至漢代華夏之羌人概念變遷 173
華夏邊緣羌人地帶之形成:東漢晚期至魏晉 177
羌人帶的萎縮:漢化、番化與夷化 179
羌人帶上最後的「羌人」 188
民國時期民族調查者所發現的羌民 197
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 206
第七章 本土根基歷史:弟兄祖先故事 211
根基歷史 214
村寨中的弟兄祖先故事 215
根基歷史的內在結構 231
「弟兄祖先故事」中的歷史心性 241
第八章 羌族認同與英雄祖先歷史 251
20世紀上半葉羌族認同的萌芽 252
老實的蠻子︰周倉與孟獲的子民 269
漢族的拯救者︰李冰與樊梨花的後代 274
古老的華夏:大禹子孫 277
過去很強大後來被打敗的羌族 283
流傳羌族中的兩種神話傳說 288
羌族認同及其本土歷史記憶 293
文化篇 297
導言 298
第九章 古羌人文化:事實、敘事與展演 301
社會記憶中的古羌人文化 302
古華夏對羌文化的描述 308
文化誇耀與模仿:北川羌人的例子 311
近代羌文化探索與書寫 316
近代羌民文化探索︰宗教信仰 327
在差異體系中尋找相似 331
異文化書寫中的華夏邊緣建構與再建構 334
第十章 當代羌族認同下的文化再造 339
羌族本土文化建構的背景 340
羌族文化再造︰語言、文字 343
羌曆年與鍋庄舞 345
羌族婦女服飾 349
飲食文化︰北川的例子 353
天神、白石信仰、端公與祭山會 355
文化展演 358
結語:歷史的創作物與創作者 367
華夏邊緣的歷史與「歷史」 368
另類「歷史」 371
歷史與「歷史」下的近代產物 374
華夏邊緣的省思:人類生態觀點 379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384
中國民族的再思考 386
參考書目 391
索引 409
我與本書作者王明珂先生應是相隔一世代的人,我的學術研究歷程是成長於1970年代以前,所以我對「民族」、「族群」等概念應是屬於「客觀文化特徵」派的;王先生的學術研究歷程是成長於1970年代以後的,所以他的「民族」、「族群」概念明顯是較偏於「主觀認同」派的。因此,朋友們與同行們,無論是與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輕一兩世代的人假如看到我為王先生這本明顯是解構文化特徵論的《羌在漢藏之間》的著作寫序,想必會為我捏一把冷汗。不過我自己倒是心平氣和,而且十分高興願意為這一本難得兼具民族史、歷史人類學及族群研究的當代「典範」大著作推介。
其實,我早已讀過王明珂先生先前的一本著作《華夏邊緣》,很能理解他的論點,而且很欣賞他能挑選「羌族」這個例子來發揮他的理論分析,所以也曾設法支持他在「羌族」中進行更長久的田野工作。如今他又把他更豐富的實地研究資料組織起來寫成本書,把他的族群邊緣理論藉羌族的「歷史」演變舖陳得淋漓盡致,使人讀來不但興趣盎然不忍釋手,而且每讀完一章都會引起不斷的反思與聯想,這也就是本書最大的特點,能讓背景不一樣的人也樂於閱讀。
王先生在本書一開始就說明這是一本以「族群邊緣理論」來探討分析所謂「羌族」的歷史民族誌,他從古代中原的漢族與西方各民族長久互動的歷程入手,透過人類族群之間資源分享與競爭關係所產生的認同與區分現象的辯解,以及「文化展演」過程的促進,再加上對當代國族主義形成的剖析,從而對今日所謂「羌族」的出現有極精采的論述,同時也對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的起源與形成提出一種全新而將引起更多反思與爭論的歷史人類學詮釋。
首先王先生認為所謂「羌人」或「羌族」在歷史上實際是一個模糊而不斷變動、飄移的群體,他們之所以成為當代的「羌族」,其實是經過三個步驟而成:最早在商代至秦漢的所謂「羌人」,其實是中原華夏族群對西方異族的統稱,他們的範圍隨華夏領域擴大而西移;較後代又因為有藏族的崛起,羌人即成為漢藏兩族之間的族群緩衝地帶,也就是所謂族群的邊緣,隨兩族勢力的消長而改變其範圍。第二步驟是在西方國族主義影響下,中國民族誌的書寫,形成核心與邊疆少數民族的體系,傳統的「羌族文化」或「氐羌文化」遂被建構成為邊疆某一少數民族的文化。最後,則是在1960年代的民族分類劃分下,「羌族」成為55個少數民族之一以後,他們自己也在文化交競展演的過程中,創造本土的文化形象而定下形來。這種族群的形成雖然複雜而曲折,但作者卻能利用他從1994年至2002年連續九年間長久而詳細的田野實地調查與文獻資料探索,很巧妙而動人地把「羌族」人飄移、模糊而至於「定型」的故事刻劃得絲絲入扣,其間他利用了很多有趣而深刻的例子來襯托出複雜的現象,例如他的「毒藥貓理論」, 「羊腦殼」與「牛腦殼」故事,「弟兄故事」與「祖先英雄」傳說,以至於所謂「一截罵一截」的現象等等,都能引起讀者會心一笑的體認。作者這些詳盡的田野資料不但能引起一般讀者的共鳴,也使我們自認為是田野老手的人類學家至為折服,雖說作者卻一再自謙說他並非是一個人類學家。
作者在本書中除努力為「羌族」的「民族史」或「民族誌」做剖釋外,另一重要的目標則是藉「羌族」的形成過程之分析進而為「中國民族」或「中華民族」等概念作「族群理論」的探討與解構。很明顯的作者是一位較近於所謂「近代建構論」的學者,所以在他的觀念中「中華民族」實是西方「國族主義」影響下的自我想像建構的產物,因此他說:
19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憂心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之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首先在革命人士心目中,指的是傳統「中國」概念中受四方蠻夷包圍的「漢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頁155-156)。
又說:
「歷史實體論」所主張的「民族」定義是值得懷疑的。近三十年來的人類學族群研究,說明無論「族群」或「民族」皆非客觀的體質、語言與文化所能界定,基於此民族定義所建立的「民族史」,一個民族實體在時間中延續的歷史,也因此常受到質疑。一個人群的血緣、文化、語言與「認同」有內部的差異,而且,在歷史時間中,有血緣、文化、語言與「認同」的移出,也有新的血緣、文化、語言與「認同」的移入;究竟,是什麼「民族實體」在歷史中延續?「歷史實體論」在學術上的缺失,主要在於將「文本」(text)與「表徵」(representation)當作「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與「民族誌事實」(ethnographical truth),忽略了「歷史文本」的社會記憶本質,以及「文化表徵」的展演本質——也就是忽略了兩者之產生與存在的歷史情境與社會情境(頁386-387)。
對於這樣的論點,國族主義的支持者,以及民族實體論者必然不大願意接受。不過,我個人倒是覺得無論你接受或是不接受,審慎閱讀作者在全書中精細、不厭其煩地反覆辯析與論述,應該會使你對「民族」、 「族群」等概念有較寬廣且較具彈性的認識。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民族」、 「族群」這樣的概念本來就像人類早期對宇宙萬物的認知分類一樣,是把一個連續譜來作一種主觀的切割,所以經常因認定者的基本立場的不同而異,因此民族的歸類就有「他人分類」與 「自我分類」之別。「他人分類」又可分為行政分類或政治分類、學者分類與他族分類等等,而「自我分類」則可因本身身份之不同,譬如知識分子、權力掌握者或是一般民眾而異,更可因空間與時間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別。以蘭嶼或澳洲的塔斯瑪尼亞的那種孤立的小島而言,人群的分類與認同不論是「自我」或「他人」的,都不致於有太大的差別,而其文化特徵,無論是有形的文化,或者無形的深層價值判斷、宇宙觀等等,也是會較有長久的連續性存在。不過在像中國或亞洲大陸東半這樣大的一個區域中,又經過幾千年的歷史演變的過程,其間族群的認同與分辨自然是極為複雜,確實很難用單一分類的觀念就可以說明清楚。所以王明珂先生這本書正可提供讀者一個回顧反思長久存在的「我族」或「他族」觀念的有利架構範式,譬如說在傳說中與「羌人」同樣被認為是夏后氏或禹王之後的「越人」,卻沒有像「羌人」那樣成為華夏邊緣領域飄移不定的族群,而在歷史上卻成為許多群體的所謂「百越」,這是因為南方沒有一個較強大的藏族存在之故?或是由於華南地理環境所致,即是可以根據本書作者的方法再加探討發展的另一個華夏少數民族互動的範例。
然而本書作者也不是一位「近代建構論」的絕對支持者。他認清楚建構論者至少有兩大缺失,其一是他們忽略了歷史的延續性與真實性面向,其二他們也忽略了對人類族群生活的現實關懷;甚至在意識型態的敵對中,解構他者的歷史整合成為一種有文化偏見的表述,甚而成為思想與政治上的對抗工具。因此,作者撰寫本書的最終企圖實際上是要更進一步超越建構者的立場,而以人類資源分配、競爭以至於共享的觀點來思考問題,並求在平心探討中達到現實的關懷與族群關係倫理價值受到尊重與強調的境界。所以他說:
在現實的關懷上,對於一個族群或民族研究者來說,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有共同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信念的人群。我們不能不關心他們目前在整體社會族群關係中的處境,以及,此種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因此在這本書中,無論是說明一條溝中各個村寨人群之認同與區分,或是以「羌」為邊緣的華夏認同及其族群邊界變遷,我都將強調其在人類資源分配、分享與競爭關係上的意義。相信這樣的歷史民族誌知識可以幫助人們思考:我們所宣稱的「統一」(或多元一體)中是否存在各種文化偏見、本位主義,導致「一體」之內的人群階序化,並造成各種形式的不平等?我們所主張的「分離」,是否為一種壟斷資源的自利抉擇,並可能導致內外族群體系之長期分裂與對抗?如此,我們才可能共商如何建立一個資源共享、和諧平等的社會體系(前言xxii-xxiii)。
又說:
在近代中國國族之建構中,華夏與傳統華夏邊緣合一而成為「中華民族」,可說是此地區長程人類資源競爭歷史中的一種新嘗試——將廣大東亞大陸生態體系中相依存的區域人群,結合在一資源共享之國家與國族內。以此而言,晚清部分革命黨精英欲建立一純漢國族國家之藍圖,以及當代鼓吹中國少數民族獨立的言論,並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同樣的,歐亞大陸之東、西兩半部有如下差別——西方為沿大西洋岸少數富強而講求人權、自由的國家,內陸則為常捲入宗教、種族與經濟資源戰爭,及內部性別、階級與族群迫害頻傳的各國、各族;東岸則為一「多元一體」的中國,以經濟補助來減緩內陸地區之貧困與匱乏,並以國家力量來維持族群間的秩序。我們也很難說,歐亞大陸西半部的體制,優於東半部中國國族下的體制(頁389)。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不僅批判、解構歷史實體論,同時也不為近代建構論所囿限,而實際上是超越了兩者的境界,進而從未來世界族群和諧平等共處的觀點來「籌謀改進或規劃更理想的人類資源共享環境」,這是何等開闊的胸懷!所以作者認為在國族建構過程中「中華民族」假如有意義,其意義應在於嘗試將廣大大陸生態體系中相依存的區域人群,結合在一資源共享互助的國家與國族內。同時他更指出歐亞大陸東西兩半的體制未必是西歐優於東亞,西方沿大西洋岸雖有講究人權、自由的富國,但其內陸則常捲入宗教與資源競爭的迫害與爭鬥之中;然而東亞卻能以「多元一體」的國族主義理想,以經濟支援及行政力量來減輕內陸的貧困與匱乏,並維持族群的秩序。假如以不具文化偏見的立場論,東亞的體制實有其長遠發展的意義。很顯然這樣的思考方式對於西歐習慣於一國一族體制的學者來說,甚而對於謀求更公平境界的「全球化」人士而言,應該都是可以促進他們反思與籌謀的典範思考。
觸及東西文化體系的差異,不免使我想起已故著名考古學者張光直教授的東西文明「延續性」與「斷裂性」的創見。張先生以這對觀念來說明新石器時代進入金屬器時代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之東西文化的差別。所謂「延續性」與「斷裂性」是指很多方面的文化現象,但是最重要的則是指金屬器發明之後生產工具的變化而言。西方文化從野蠻進入文明的代表是兩河流域的「蘇美」(Sumerian)文化,蘇美的金屬器發明應用在農業的生產工具上,而與較早期用石器於生產是有明顯的不同,所以在工具性質的利用上是一種斷裂;但在中國,金屬青銅器在黃河流域出現的夏末商初起用之時,是用在政治與宗教儀式上,而生產工具則仍沿用原有的石、木、骨、蚌等,所以說是一種延續,而這種延續的關係也同時表現在人際關係、文字的應用、城鄉關係、財富累積與集中、權力的獲得以至於意識型態的表現上(參看其〈延續與斷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一文,1986)。要立刻以張先生的這種「延續性」與「斷裂性」文化傳統差別的說法與上述本書所強調的東西族群關係模式的差異勾連起來也許較不易理解,但是假如把我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致中和宇宙觀」模式的論證,或稱「三層面和諧均衡宇宙觀」的尋求對自然、對人群、對自我三層面的和諧均衡的理想境界來對比說明,也許就較易於理解在東亞大陸境內自古以來一直有一種融合自然、人群,甚至超自然於一體,而企圖共同分享資源與文化經驗的傳統在不斷「延續」之中(參見〈傳統宇宙觀與現代企業行為〉一文,1994),這也許就是本書作者所說的當前「多元一體」國族主義的歷史根源吧。總之,作者在本書中的種種論述確能引起許多學術的反思與共鳴,這應是本書最值得推薦的特點,希望讀者能從本書的閱讀中不僅欣賞作者的細膩論述與寬廣的理論架構,同時也能藉此對族群關係脈絡有更多的反思與體認。
李亦園
2003.1.20草於台北南港中研院
前言
本書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誌;更正確的說,這是一本描述與詮釋「華夏邊緣」的歷史民族誌。本書不只是描述羌族,一個中國大陸上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更主要的是,我希望透過羌族及其歷史來說明漢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邊緣的形成、變遷及其性質。本書更大的野心是,由人類資源分享與競爭關係,及其在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上的表徵(representations),來說明人類一般性的族群認同與區分。最後,基於這些對「族群」(或民族、社會)、「文化」與「歷史」的新理解,我對於當代漢、羌、藏之間的族群關係,或更大範圍的中國民族的起源與形成問題,提出一種新的歷史人類學詮釋。
作為中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約有20萬人,主要聚居於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東南隅與北川地區。他的南方是分布於川、滇、黔三省,人口約658萬的彝族。他的西方是人口459萬,分布於中國四分之一土地的廣大藏族。他的東方則是更廣大的12億漢族——可能是全世界宣稱有共同祖先的最大族群。目前許多漢族及少數民族學者皆認為,羌族與漢族、藏族、彝族,乃至於納西、哈尼、景頗、普米、獨龍、怒、門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諾、阿昌等十餘種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關係。而羌族民眾也常自豪,稱「我們羌族是漢族、藏族、彝族的祖先」。為何,一個當前人口不過20萬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個民族共十數億人聯結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將說明造成此現象的歷史與「歷史」。
我以加括號的「歷史」來與歷史作區分;歷史是指過去真正發生的一些自然與人類活動過程,而「歷史」則指人們經由口述、文字與圖象來表達的對過去之選擇與建構。在本書中,我將一再探索歷史過程,與「歷史」建構過程,以及兩者間的關係。以此而言,本書之作近於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在歷史人類學中,如舍佛曼與古立佛(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所言,研究的焦點可分為兩大主題:一、「過去如何造成現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d the present);二、「過去之建構如何被用以詮釋現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 。在本書中,我探討的主要問題便是:什麼樣的歷史造成當今的羌族?什麼「歷史」被不同的群體建構,來詮釋、理解當今羌族?以及,對羌的「歷史」建構與再建構,如何造成並改變歷史上的「羌人」與「華夏」。
在本書中,不只是對「歷史」,我也將對「民族」與「文化」提出一些新見解。如果對「民族」、「歷史」與「文化」抱持著傳統的定義,那麼我可能寫出一部可與「中國民族史」接軌的「羌族史」;我的田野資料也能寫出一本可作為「中國少數民族叢書」之一的「羌族民族誌」。然而,讀者將發現,在本書中我不斷的檢討、解構與再建構我們對「民族」(以及族群、社會)、「歷史」與「文化」的一些既有概念。近年來,在解構「民族」與國族主義(nationalism)研究之風下,學者常指出許多所謂的「傳統」事實上是近代的創造,而「民族」則是近代國族主義風潮下知識菁英們的想像群體 。基本上我同意這些看法。然而這些「創造」與「想像」的近代之前歷史事實與相關歷史記憶基礎,以及「創造」與「想像」過程與此過程中各種社會權力關係,以及更重要的,相關的資源分享與競爭背景,都值得我們再深入探索。這樣的探索必然超出「近代」與「歷史」的範圍,而須兼及更早的歷史與歷史記憶,以及人類學的田野研究。
對傳統「民族」、「歷史」以及「文化」概念的質疑,曾使我,一個歷史學者,在歷史文獻中窮究羌族歷史十五年之後,又走向近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近八年來,在中央研究院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幾度前往羌族地區作田野調查研究。或翻山越嶺探訪各深溝村寨中的住民,或在汶川、茂縣、理縣等山間城鎮中與當地知識分子交談,目的都在探索「羌族」對本民族及其歷史與文化的看法。田野經驗讓我鮮活的觀察、體驗到「文化」與「歷史」的建構過程,及其背後多層次的族群認同與社會區分體系,以及此中涉及的許多個人與群體之利益與權力關係。此知識解構了我自身原有的各種文化與學術偏見。然後,藉此反省,我重新閱讀歷史文獻——由一種「在文獻中作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的角度,考察這些作為「社會記憶」的文化與歷史書寫遺存,探索其背後個人或群體間的利益與權力關係,社會認同與區分體系,並嘗試了解相關的「文化」與「歷史」建構過程。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會篇」,主要在介紹本書的主體——羌族;描述他們的地理分布,環境與聚落型態,資源競爭與分享體系,以及因此產生的社會認同與區分等等。這一部分,可以說是本書有關羌族歷史與文化探討的「民族誌」基礎。然而,基本上我不是一位人類學者或民族學者,我也難以寫出一部當代人類學或古典民族學的民族誌(ethnography)。作為一位研究族群現象的歷史學者,在田野調查中我關心的主要是歷史與族群的問題;所有關於羌族體質、語言、文化、宗教與經濟生活的觀察與探討,都被納入歷史與族群的關懷與思考脈絡之中。
這種關懷與思考,源於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論爭議。一個較傳統的「民族」概念,經常將民族視為一群有共同體質、語言、經濟生活與文化等客觀特徵的人群。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便是一個例子。這樣的民族概念,在許多學術研究中仍被奉為圭臬;更不用說,在一般民眾中這樣的觀點更是普遍。西方社會人類學界對於族群現象的探討,由於費德瑞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人的貢獻 ,基本上在1970年代以後就遠離了以客觀特徵界定民族的研究傳統,而著重於族群主觀認同的形成與變遷。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學者們曾爭辯於究竟族群認同是人類資源競爭與分享關係中的功利性工具,或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無可選擇的根基性情感;這便是「工具論者」(instrumentalists)與「根基論者」(primordialists)之爭。事實上,這些爭論已指出了族群認同的兩大特質——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資源環境變化而改變;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認同有時不易改變,且常掩蔽人群間其它社會認同與區分(如性別、階級與地域)。
1980年代中期以來,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歷史」與族群認同之間的關係,因此也化解了「根基論者」與「工具論者」的爭論。人們以共同的起源「歷史」,來模擬人類最基本的「手足之情」;這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由來。另一方面,「歷史」作為一種社會集體記憶,它可以被選擇、失憶與重新建構,因此族群認同可能發生變遷 。無論如何,族群認同背後的政治權謀(politics)與歷史(history)因素成為關注的焦點;這也順應當代人類學的一般發展傾向 。
認同(identity)與區分(distinction)是本書「社會篇」的主題。認同,是指一個人在特定情境下,認為自己屬於一個社會群體;區分則是,相反的,在特定情境下人們將我群與他群體之成員區別開來。可以說,認同與區分是人類社會結群現象的一體兩面。空間、資源環境,與人群在其間的資源分配、分享與競爭體系,是人類社會分群的主要背景。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間,各個家庭、家族與村寨等群體,都在資源共享與劃分體系中凝聚、區分與延續。家族神、山神、廟子與菩薩等信仰,強化這些族群區分並維持族群界線。因而在本書中,我所關注的與探討的不只是狹義的族群(ethnic group)與「族群本質」(ethnicity),而更是在一層層「邊界」(boundaries)包圍中人們的各種社會認同與區分。
關於人類社會「區分」的問題,在人類學與社會學界有一個研究傳統,其中包括諾勃特.伊里亞斯(Norbert Elias)、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皮耶.博爾都(Pierre Bourdieu)與日內.吉哈德(René Girard)等著名學者的研究 。這些關於人類社會區分,以及相關的品味、生活習俗、歧視、仇恨與暴力的研究,被大多數「族群本質」研究者忽略了。這主要是由於,上述學者們研究的是一社會中不同階級、性別或新舊住民等親近群體間的區分,而非「族群」或種族區分。在本書中我由羌族「毒藥貓」傳說與信仰來說明,「區分」不只是存在於各家族、村寨間;每一個人都是與外界有區分的孤立個體,生活在險惡的環境與可能有敵意的鄰人與親屬之中。人們並不經常能夠,或願意,理性分辨外在威脅與敵意是來自那一層「邊界」之外。因此與鄰人、親人的矛盾與仇恨,可能轉嫁到遠方的「異族」身上;相反的,對遠方「異族」的仇恨與恐懼,也可能投射在對身邊鄰人與親人的猜疑與歧視上。所有敵意與仇恨的轉嫁、遷怒,強化層層邊界以凝聚各層次的人群。我由此建立一「毒藥貓理論」,以詮釋人類之族群認同,以及相關敵對、歧視與集體暴力現象的社會根源,並以此補充吉哈德等人「代罪羔羊理論」之不足。
本書第二部分是「歷史篇」。「社會篇」所描述的羌族,事實上是歷史與「歷史」的產物。我認為,唯有了解什麼樣的歷史過程與歷史記憶造成當今羌族,我們才能全面的了解羌族。不但是今之羌族,也包括古代羌人;不但是羌人與羌族,我們也能因此了解華夏與中華民族。這是一個歷史人類學的羌族研究,也是我所謂的「華夏邊緣」研究。
在許多中國學者的歷史知識中,羌族是一個居於華夏西方的異族;這民族幾經遷徙、繁衍,並與周遭民族融合而形成許多新民族。這樣的羌族史,說明部分漢族、藏族、彝族,與其他許多西南少數民族的祖先源流。在這民族史中,民族被認為是一有共同體質與文化特徵的人群,並在歷史中延續、成長、消亡。然而,類似的「民族史」在有後現代主義傾向之學者眼中,卻只是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國族主義下的集體想像與建構。後現代的中國民族與民族史研究,便在於解構這樣的「歷史」。究竟,羌族是歷史的產物,或是「歷史」的產品?
對此,我的看法是:當前之羌族為歷史之產品,也是「歷史」之創造物。不僅如此,他們也是歷史與「歷史」的創造者。國族主義下的「歷史」想像創造當代羌族,並凝聚羌族。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晚清以前中國文獻中對「羌」的記載都毫無意義。「羌」這樣的西方異族稱號,存在於商人、華夏或中國人之歷史記憶中至少有三千年之久。由這些人群對「羌」的描述與記憶中,我們可以探索華夏或中國人西方族群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也就是說,由「族群邊緣」觀點,近代國族主義下漢族對羌族之歷史與文化建構,反映漢族對其族群邊緣的重新塑造。相同的,歷史上中國人對「羌」的描述,也反映當時中國人對其西方邊緣人群的刻畫。被華夏想像、刻劃的「羌人」,也以行動締造歷史,以及想像、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
在本書中,我所強調的羌族史不僅是漢族西方族群邊緣的歷史,也是藏族的東方族群邊緣歷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氐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邊緣的歷史。在這歷史中,「民族」是一群人的主觀想像與建構;想像與建構我群的共同祖源與歷史,以凝聚「同質化」的族群,以及想像、建構他群的祖源與歷史,以刻劃「異質化」的族群邊緣。如此,一個個由「歷史記憶」所造就的個人與群體,在資源競爭與分配體系中彼此合作、妥協、對抗,並運用策略與權力影響彼此的歷史記憶,因此產生新的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在我所發掘與重建的歷史中,傳統「民族史」中的歷史主體「羌族」似乎並不存在。的確,沒有一個那樣的「民族」在歷史中延續。當代羌族與羌族認同,為上述華夏西部族群邊緣歷史之最新階段產物。然而這並不是說,歷史上的「羌人」並不存在。歷史上被華夏稱作「羌」的人群,世代生息於華夏西部「漂移的族群邊緣」上,他們的後裔因此散在今日之羌、漢、藏、彝及其他民族之中。我們也不能說,當今羌族只是背動接受主體民族所給予的「歷史」才成為羌族;或是說,在成為羌族之前他們是沒有「歷史」的人群。當代羌族的本土「歷史」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英雄祖先歷史」,另一類是「弟兄祖先故事」。在英雄祖先歷史中,他們或藉由「過去」來呈現自身的邊緣弱勢形象(如愚笨的蠻子),或藉由「過去」來塑造足以為傲的我族形象(如漢族的拯救者與守護者)。無論如何,這些「歷史」多起源於一個「羌族」英雄祖先——如周倉、樊梨花或大禹。
在羌族中,另有一種「歷史」——弟兄祖先故事。它們以「從前有幾個兄弟到這兒來,分別建立自己的寨子……」諸如此類的「歷史」,來說明幾個寨子的村民起源與彼此之祖源關係。我稱之為一種「根基歷史」(primordial history);它們以「共同起源」強化族群成員間如兄弟手足般之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中國西南各民族傳說中,或世界各地民族傳說中,這一類「弟兄祖先故事」都非常普遍。只是在我們的知識分類系統裡,它們被歸類為傳說或神話;「英雄祖先歷史」,才被認為是真正發生過的歷史。這種偏見,忽略了「英雄祖先歷史」也被用來凝聚「同胞手足」之情(同時也被用來將人群階序等差化),它們也是一種根基歷史。事實上,「弟兄祖先故事」與「英雄祖先歷史」可以說是兩種不同「歷史心性」之產物。藉此,在本書中我也將探討歷史心性的問題。
本書第三部分為「文化篇」。過去許多學者皆將「傳統文化」視為一民族在歷史傳承中所得之祖先遺產。然而當代學者卻傾向於相信,所謂「傳統文化」經常是近代國族主義下知識分子的主觀想像與創造。前者的看法,固然是受誤於國族主義下以客觀體質、語言、文化特徵來界定的民族概念。後者,則忽略了近代「歷史」、「文化」創造的古代基礎,以及「創造」背後的社會權力關係與過程。
在本書中,我由三個角度來解讀文獻中有關「羌人文化」的描述。在事實(fact)層面,一段華夏對羌文化的描述,可能反映當時被稱為「羌」的人群之真實習俗。在敘事(narrative)層面,這些有偏見的選擇性異文化描述,可能反映華夏自身的文化與認同特質。在習行與展演(practice & performance)層面,華夏對異文化之污化描述(無論是否真實),在歧視、誇耀與模仿等文化展演作用下,促成「羌人」學習、模仿華夏文化與歷史記憶而成為華夏。「羌人文化」便如此,永遠在一個不斷建構與變遷的過程中。這樣的建構與變遷過程,也造成今日之羌族與羌族文化。在此「文化史」中延續與變遷的並非一個民族的文化,而是一個在核心與邊緣族群關係下的文化展演、誇耀與模仿過程。或者說,在此歷史中延續與變遷的,是各種核心與邊緣群體間的社會本相(social reality)之文化表徵。
將「文化」視為透過各種媒介的展演,我們才能見著「文化」動態的一面,並超越「客觀文化現象」與「主觀文化建構」之對立。客觀文化在展演中被人們主觀認知、批評與模仿,由此塑造或改變人們的認同;個人的主觀認同,也透過文化展演而社會化、客體化。
在田野研究中,我曾得到許多羌族朋友的幫忙。而我,一位解構「典範歷史與文化」的學者,在構思本書時最感到不安的便是:如果他們的民族自尊與驕傲建立在這些典範羌族史與羌族文化知識之上,那麼,是否我的著作會傷害到他們的民族認同與感情?然而,我希望讀者與我的羌族朋友們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可以發現我並非只是解構「羌族史」或「中國民族史」,而是在更廣闊、更具詮釋力的認知體系上,重新建構一個關於「羌」的歷史或歷史民族誌知識。這個新的歷史與歷史民族誌,可以讓我們對於「羌族」、「漢族」、「藏族」或「中國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而,本書之論述必須置於「華夏邊緣」歷史中,才能完整呈現我對於羌族與中國民族的見解。事實上,這本書可說是我在1997年出版之《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之延續與補充。在前書中,我首先提出一個華夏「邊緣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構想,然後,以此說明華夏邊緣的出現及其漂移、擴張與變遷過程;以及解釋在資源競爭與各層次權力爭衡背景下,華夏邊緣之擴張與變遷如何藉邊緣人群的歷史記憶與失憶來進行。本書便是以漢、藏之間的古今羌人與羌族為例,說明一個華夏西方族群邊緣的形成與變遷。因此這不只是一個「羌族」的歷史,也是「藏族邊緣」與「漢族邊緣」的歷史;這不只是「外夷」或「少數民族」的歷史,它也是華夏與中國民族歷史的一部分。
近20年來,在「中國民族」或「中國少數民族」之歷史與民族學研究中,流行著兩種彼此對立的解釋模式。第一種,我且稱之為「歷史實體論」,另一則是「近代建構論」。「歷史實體論」者主張,中國民族是在歷史上延續之實體;其中包括一歷史悠長的核心漢族,及許多在歷史中起落興衰,並與漢族互動、融合的邊疆少數民族。此解釋模式幾乎被所有中國歷史與民族學者所採納;相關的「歷史」,便是典範中國史與中國少數民族史。近年來,有些受「創造傳統」(invented tradition)與「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等研究影響的西方學者則認為,中國民族或中國少數民族是近代國族主義下的建構物。他們強調,近代中國政治威權下的民族分類與相關歷史建構,將許多原外於中國的大小非漢族群歸納、劃分成一個個「少數民族」 。在族群政治立場上,上述兩類學者也常針鋒相對;前者常指責西方學者試圖破壞中國之民族團結,後者則指責中國政府(及大漢族主義學者)藉著「歷史」控制甚至欺壓少數民族。
這兩種論述,基於不同的民族與文化研究理論。在本書中,我對民族與文化的理解,與近代建構論者有較多相似之處——基本上,我無法同意歷史實體論者的典範「中國民族史」。然而,我認為近代建構論也有許多值得修正與補充之處。其主要缺失有二。其一,研究者忽略了歷史的延續性與真實性面向。其二,研究者也因此忽略對人類族群生活的現實關懷;甚至在意識型態的敵對中,「解構他者歷史」常成為一種有文化偏見的表述,或思想與政治上的對抗工具。近代建構論者的這兩個缺失,原為歷史實體論者所長。但遺憾的是,歷史實體論者所主張的延續性歷史,是在某種中心主義下(如男性、士大夫或華夏中心主義)之選擇性歷史記憶建構。因此它的「現實關懷」——如安邊、治邊與化夷等等——也常流於政治干涉、掌控與文化歧視。
在本書中我所建立的民族史知識,是一個核心與邊緣關係下的「華夏邊緣歷史」,或「漢藏邊緣歷史」。藉由這個歷史,以及它殘留在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中的社會、文化與歷史記憶,我說明歷史上漂移的、模糊的華夏邊緣「羌人」,如何轉化為具有漢、藏、彝及許多西南民族間之橋樑性質的「羌族」。「羌人」與「羌族」是一個不斷變遷的「邊緣」——他們與青藏高原東緣的一些部落、村寨人群是華夏之族群邊緣,也是吐蕃與藏族的族群邊緣。在此,歷史是延續的;但在歷史中延續的並非一個「民族」,而是一個多層次的核心與邊緣群體互動關係。在此,「羌族」的歷史或被解體為華夏與藏族邊緣變遷史,「羌族」本土文化或也被描述為易變的、多元的、模糊的。然而就是這些歷史主體的變遷與不確定性,以及文化之模糊性,說明在中國西方與西南邊疆的漢、藏之間,或漢與非漢之間,原有一個漂移、模糊的族群邊緣。在近代國族主義之下,它才轉化成漢、羌、藏、彝各民族間的族群界線。這樣的知識,不同於「歷史實體論」與「近代建構論」之主張;其目的並不在於爭辯或解答「中國少數民族」或「中國民族」的歷史真實性,而是說明「中國少數民族」與「中國民族」的形成過程。在此過程中,無論是「羌族」或「中國民族」都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創造物。
在現實的關懷上,對於一個族群或民族研究者來說,我們所研究的對象是一群有共同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信念的人群。我們不能不關心他們目前在整體社會族群關係中的處境,以及,此種族群關係的歷史演變。譬如,在當代羌族認同形成之前,本地各溝各寨人群常在相互歧視、仇殺之中,對此老一輩羌族人民記憶尤新。如今他們常說︰「這都是由於過去的人沒知識,不知道大家原來是一個民族。」這些話可以讓我們深思:若非是有更好的族群關係理想,我們何須解構這些「知識」、這個「民族」?的確,由傳統華夏邊緣的「蠻夷」蛻變為「少數民族」,人群間的歧視與暴力已消除不少。然而作為「少數民族」之羌族,在整體中國仍居於邊緣地位;他們在現代化的邊緣、政治邊緣,也在核心族群的邊緣。因此在這本書中,無論是說明一條溝中各個村寨人群之認同與區分,或是以「羌」為邊緣的華夏認同及其族群邊界變遷,我都將強調其在人類資源分配、分享與競爭關係上的意義。相信這樣的歷史民族誌知識可以幫助人們思考:在我們所宣稱的「統一」(或多元一體)中是否存在各種文化偏見、本位主義,導致「一體」之內的人群階序化,並造成各種形式的不平等?我們所主張的「分離」,是否為一種壟斷資源的自利抉擇,並可能導致內外族群體系之長期分裂與對抗?如此,我們才可能共商如何建立一個資源共享、和諧平等的社會體系。
如此兼及歷史、民族誌與現實關懷的他者描述書寫傳統,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史記》之四裔列傳中。在近代國族主義下,此傳統結合外來之社會科學,曾化為歷史學、民族學(或人類學)與邊政研究等中國少數民族研究傳統。這些「邊緣書寫」,曾造成華夏邊緣與此邊緣的歷史變化。在本書中,我以結合歷史記憶、歷史事實與歷史心性之長程歷史研究為經,以人類資源生態與社會認同區分體系為緯,共同構成一種歷史民族誌研究。從某一角度來說,它仍是結合歷史、民族誌與現實關懷的書寫。但「社會」(或民族)、「歷史」與「文化」在此研究中都有新的理解與詮釋;漢族中心主義的「安邊治邊」現實理想,被「如何達成族群和諧與資源共享」所取代;描述分析他者並非為了創造、刻劃我群邊緣,而是為了檢討與認識自我。無論如何,這是我近十年來在羌族研究中所得,也是我在中國民族研究中由「解構」到「重新建構」的自我反省與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