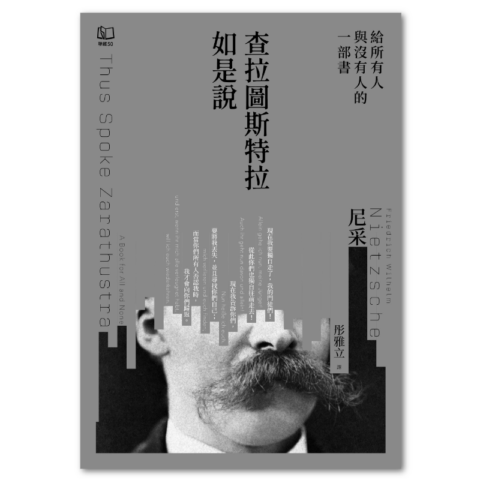論語與孔子思想
原書名:論語と孔子の思想
出版日期:2015-07-29
作者:津田左右吉
譯者:曹景惠
印刷:黑白印刷
裝訂:精裝
頁數:656
開數:25開(高 21×寬14.8cm)
EAN:9789570845860
系列:現代名著譯叢
已售完
日本知名學者津田左右吉
著眼《論語》中孔子言論的捏造、錯植與改寫等問題,
以原典批評的實證方法,
透過文本與前後時期諸史料的相互對照、比較,
釐清《論語》與孔子思想、言論的關係。
津田左右吉先生一路抽絲剝繭,先確立孔子言論,進而對孔子思想加以評析,闡述《論語》與孔子思想是如何被儒家承襲、變改、甚而運用操作,同時亦探討《論語》一書成立的原委以及儒學形成的脈絡,思考孔子思想在儒學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
津田左右吉身為歷史學暨思想史學家,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等領域多所鑽研,著述豐碩。而在研究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之際,一如本書「緒言」開頭所述,津田開宗明義表示欲通曉儒家思想,必先明白孔子思想,而要明白孔子思想,必得好好研讀《論語》。然而津田在研究考察《論語》一書的過程中,發現《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有諸多不一致與矛盾之處,似非出自孔子所言,後人假借孔子之名偽作或新創的情況不少,於是其以原典批評的實證方法,透過《論語》文本與其前後時代諸多史料典籍的相互對照比較,試釐清《論語》和孔子思想、言論的關係,《論語》一書成立的原委,並更進一步地探討儒學形成的脈絡,以及孔子思想在這樣的儒學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津田認為,過去學者們沒有注意到文本中孔子言論的捏造、錯植和改寫等問題,是研究上極大的致命傷。而在本書中,津田從最根本的問題著手,將《論語》中有哪些章句確定是孔子所言,又有哪些不是孔子所說,而非孔子所言者是在何時、又為何會被視作孔言等問題,都做了詳盡的查證與精闢的分析。一路抽絲剝繭,先確立孔子言論,進而對孔子思想的內涵加以評析,闡述《論語》與孔子思想是如何被儒家承襲、變改、甚而運用操作等問題。本書在《論語》與孔子思想關係的釐清上,特別是先秦至西漢時期孔子言論竄作改寫過程的解明等,都對現今儒學研究有實質上的助益。
作者:津田左右吉
1873-196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實證主義歷史學家,對日本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及日本古代史等領域鑽研甚深,研究能量旺盛,論著等身,歿後由岩波書店出版了《津田左右吉全集》全三十三卷(1963-1966),再版(1986-1989)時並追加了補遺兩卷。
譯者:曹景惠
生於台灣台北。畢業於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日本岡山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日本中世文學、和漢比較文學,主要著作:《日本中世文学における儒釈道典籍の受容-『沙石集』と『徒然草』-》(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中譯本導讀
凡例
前言
緒言
第一篇 世間流傳的孔子言談
第一章 與論語無關的孔子言談
一 西漢時代書籍之所見
二 先秦時代書籍之所見
三 孔子相關故事裡的孔子言談
第二章 與論語相關的孔子言談
一 西漢書籍之所見
附錄 《禮記》〈坊記〉、〈表記〉、〈緇衣〉、〈中庸〉四篇的成立年代
二 西漢書籍所載孔子相關故事裡的孔子言談
三 先秦時代書籍之所見
第二篇 《論語》及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一章 西漢時代的《論語》傳承
第二章 在孟子時代以前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三篇 《論語》的型態及內容
第一章 《論語》的型態
第二章 《論語》的內容
第三章 各篇的成立與構成
第四篇 《論語》成書的經緯
第一章 在《論語》文本裡,較孟子時代為後的要素
第二章 在《論語》文本裡,較孟子時代以前的要
第三章 從《論語》的型態來看
第四章 《論語》成立的過程與其書之性質
第五篇 《論語》與儒家之學
第一章 孔子思想與儒家之學
一 孔子思想
二 孔子思想與孟子學說
三 孔子思想與荀子學說
四 孔子思想與漢儒之學
五 孔子思想與儒學的普遍傾向
六 儒學在古代中國思想中的地位
七 中國人的生活與儒學
第二章 《論語》在儒學中的地位
結語 《論語》的研究方法及態度
編輯後記
附錄一 原著中引用津田左右吉著作書目
附錄二 津田左右吉年表
附錄三 《津田左右吉全集》目錄
附錄四 津田左右吉研究相關書目
中譯本導讀(節錄)
《論語與孔子思想》(《論語と孔子の思想》)為日本近代思想史學者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一九六一)之代表著作之一,自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開始執筆,於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十二月完稿,由日本岩波書店出版,津田氏歿後收錄於《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四卷(東京都:岩波書店,昭和三十八年(一九六三))。此中譯本是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十四卷再刊本第十四回配本(東京都:岩波書店,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為底本。全書內容囊括了前言、緒言、結語與五大篇章,分別為:
第一篇 世間流傳的孔子言談
第二篇 《論語》及孔子言論之傳承
第三篇 《論語》的型態與內容
第四篇 《論語》成書的經緯
第五篇 《論語》與儒家之學
結語 《論語》的研究方法及態度
津田左右吉身為歷史學暨思想史學家,對於日本與中國的歷史、思想、文化等領域多所鑽研,著述豐碩。而在研究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之際,一如本書「緒言」冒頭所述,津田開宗明義表示欲通曉儒家思想,必先明白孔子思想,而要明白孔子思想,必得好好研讀《論語》。此乃本書執筆的契機。然在研究考察《論語》一書的過程中,津田發現《論語》所記載的孔子言論有諸多不一致與矛盾之處,似非出自孔子所言,後人假借孔子之名偽作或新創的情況不少,於是其以原典批評的實證方法,透過《論語》文本與其前後時代諸多史料典籍的相互對照比較,試釐清《論語》和孔子思想、言論的關係,《論語》一書成立的原委,並更進一步地探討儒學形成的脈絡,以及孔子思想在這樣的儒學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等問題。津田認為過去學者們沒有注意到文本中孔子言論的捏造、錯植和改寫等問題,是研究上極大的致命傷。而在此書中,津田從最根本的問題著手,將《論語》中有哪些章句確定是孔子所言,又有哪些不是孔子所說,而非孔子所言者是在何時、又為何會被視作孔言等問題,都做了詳盡的查證與精闢的分析。其一路抽絲剝繭,先確立孔子言論,進而對孔子思想的內涵加以評析,闡述《論語》與孔子思想是如何被儒家承襲、變改、甚而運用操作等問題。此書在《論語》與孔子思想關係的釐清上,特別是先秦至西漢時期孔子言論竄作改寫過程的解明等,都對現今儒學研究有實質上的助益。
以下先概述津田左右吉生平與其畢生研究成果,再簡介《論語與孔子思想》各篇內容,進而檢討《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在當代思想史中的座標位置。
一、津田左右吉其人與學
津田左右吉生於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十月三日,岐阜縣加茂郡栃井村(現美濃加茂市下米田町)舊士族之家,歿於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十二月四日,享年八十八歲。津田家原為尾張德川家家臣仕醫,屬下級武士,明治維新後歸農,其父津田藤馬漢學素養豐厚,在文明義校(後改為文明學校)擔任教職,左右吉四歲起即在父親的教導下背誦漢詩文。後進入地方上的文明小學校就讀,直接受教於隸屬名古屋山崎派的漢學後代——森好齋先生,接著進入名古屋的私塾、私立中學學習。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畢業於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政治學科,是年認識京都大學校長沢柳政太郎教授,借居其寓所,並在沢柳教授介紹下師事東洋史學家白鳥庫吉先生。青年時代津田左右吉曾任富山縣東本願寺別院附屬教校、群馬縣立中學校、千葉縣立中學校等校教員,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則赴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在白鳥庫吉主導的滿鮮歷史調查室擔任地理歷史調查員,正式邁入研究生涯。
自任滿鮮調查員開始,津田除了考察朝鮮的歷史地理,亦開始關注日本文化的起源與發展過程的相關問題,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出版了第一本研究專書《神代史的新研究》(《神代史の新しい研究》),開啟了津田長年的學術著述生涯。其後數年間陸續刊行了日本思想史上的名著《文學中所展現國民思想之研究》(《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共四冊(一九一六─一九二一),並繼神代史之後著手進行古代史的研究,於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完成《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的新研究》(《古事記及び日本書紀の新研究》)(洛陽堂)一書。此書刊行前一年,即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津田就任早稻田大學講師,至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因筆禍事件退職為止,專授東洋哲學課程,同時其思想史研究範疇也擴展至古代中國。戰後發表了數篇有關中國儒教的論文,相繼出版了《道家思想及其展開》(《道家の思想とその展開》)(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左傳的思想史研究》(《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昭和十年﹝一九三五﹞)等探討古代中國思想的專著。同時,津田亦重新修訂舊作,自一九二四年開始陸續再版了《神代史研究》(《神代史の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研究》(《古事記及日本書紀の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社會與思想》(《上代日本の社会及び思想》)等日本上代史研究四部作,後因被控著作內容冒瀆皇室尊嚴而遭禁售,並與出版社岩波書店社長岩波茂雄先生一併被起訴。判決結果在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五月出爐,確定其因《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研究》一書判刑三個月(緩刑兩年)。津田不服判決,向東京高等法院提交「上申書」,卻因當時正值二次世界大戰戰況激烈,日本國內情勢混亂,以致訴訟程序未有所進展時效即過,於是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確定原有罪判決是為無效。然此時津田早已被迫辭去教職,由友人引介疏散移居至岩手縣平泉。戰後,其學問與研究業績再度廣受世人肯定,一九四六年當選為早稻田大學第一任公開選任的校長,津田卻堅持辭退。一九四九年則獲頒文化勳章。儘管津田聲望與地位日與俱增,他卻甚少公開露面,鎮日埋首重補修訂舊作直到晚年。
二次大戰期間津田左右吉曾因論著內容涉及對皇室不敬而被起訴,戰後卻又獲天皇授予文化勳章,其一生起伏跌宕,對學問研究的熱情卻始終不減。津田的論著在其歿後由岩波書店出版了《津田左右吉全集》全三十三卷(一九三六─一九六六),二十年後再版(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時並追加補遺兩卷,收錄了新收集的書簡資料等。以規模來說,津田左右吉的著作遠勝於東京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全集》(全十卷)、《內藤湖南全集》(全十四卷)、也超越了《吉川幸次郎全集》(決定版、全二十七卷),其研究能量旺盛,在近代東亞人文學界中堪稱第一。
雖然津田沒有受過歷史學研究的正規專業訓練,但其畢生皆投注在思想史的鑽研與著述,研究成果豐碩,影響後世甚深,當時甚至以「津田史學」一詞來囊括津田的學問,由此可見其學問獨樹一格。一般認為,所謂「津田史學」的基礎精神與研究方法,乃師承恩師白鳥庫吉先生,於滿鮮任調查員時期所培養出來的。而「津田史學」的內涵大致可分成兩個面向,一是以日本古代文獻《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為主的日本上代史研究,又稱為「記紀研究」,一是中國古代儒家、道家思想研究。這兩個研究領域看似無關,在「津田史學」中其實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津田為了釐清日本文化原貌,進一步闡釋自身對日本「國民國家」中所謂「國民」特性養成之理念,突顯日本國民國家的日本文化形象,其所採取的作法是重新考察日本古代「記紀」內涵,試圖將日本文化從漢文化圈中切割、獨立出來,而這便是津田開始研究中國思想的起點。換句話說,津田之所以會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甚至著手研究中國古代思想,追根究源其實是為了凸顯日本文化特質,確立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之不同,進而建立近代國民國家的概念,在此理念下所衍生出來的產物。
津田的「記紀研究」並非將《古事記》與《日本書紀》當作神話故事來閱讀,而是將其視為文獻史料、加以批判,透過詳細的檢討與縝密分析後,深入探討該書作者的執筆動機與意圖。津田提出天皇乃萬世一系的概念不過是「那個時代人們所構想出來的故事」,這些神話故事雖不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卻也反映了編造者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思想,深具思想史料價值。津田「記紀研究」的出發點在建立一種近代國民所應當有的天皇觀與國家觀,試圖剔除天皇制所隱含的非合理主義要素,將天皇從過去神秘主義的觀念中解放出來,並無意否定天皇存在的價值及其對於日本國民的意義。此研究結果不僅對日本史、日本思想史學界帶來極大震撼,津田援引出自近代科學理念的「史料批判」研究手法,也為當代古代史研究帶來了劃時代的進展,奠定了現今日本歷史學與人文研究的基石。
津田在「記紀研究」中所採用的「史料批判」方法,也發揮在考察中國儒道思想內涵上。津田在《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五○五─五一三頁)中曾表明其研究中國思想方法是先進行「文本批判」(原典批判)——透過與各種異本的相互對照、比較等工作來校訂文本,確立「正確的文本」(指還沒有變化成各種形態流傳或產生錯誤的記載前,最原始狀態的文本而言),再以此為基礎進行其所謂的「高等批判」,也就是分析文本內容、探討典籍的編纂目的、創作過程等問題。奠基於「史料批判」「文本批判」的「高等批判」研究方法,亦即以文獻史料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可說是支撐「津田史學」成立的重要基石。直傳弟子栗田直躬曾在津田誕辰一百二十週年紀念演講〈津田先生の学問の意味〉(收錄於《東洋の思想と宗教》一一卷一九九四年六月)中談到,津田先生的學問是以資料為主體的實證研究,與近代科學的思考模式相近,其研究方法的特色有二,其一是採「歷史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從時間(縱)與空間(橫)這兩個面向來綜觀歷史與文化的課題。另一個特色是,津田的思想研究並不只是歷史知識的堆積,其背後富含了神話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學養,有助於古典文獻的考察與多元理解。
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的思想史研究》(《津田左右吉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都:岩波書店,一九七二年)一書也將津田的學問內涵作了極深入而精緻的分析考察,認為津田受明治時期啟蒙思想影響甚深,其學問的立足點是來自十八世紀西歐重視實證理論的科學研究方法。雖然津田的「原典批判」是極為細膩的一種文獻考察方法,但早川万年先生也在〈津田左右吉的「史料批判」〉(〈津田左右吉の「史料批判」について〉)(《季刊日本思想史》近代の歷史思想特集六七號,東京都:PERIKANSHA Publishing Inc.,二○○五年六月)一文中指出,津田原則上是站在「思想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文獻的,換句話說,津田的古典研究是將文獻放在「思想發展史」上所做的評判,這種「俯瞰性的歷史批評」是「津田史學」的一大特徵,而無論是考察中國或日本思想的研究,其主軸皆歸於前述「國民」概念的建立。有別於以年代來劃分文學作品的一般作法,津田在其著書《文學中所展現國民思想之研究》中是以貴族時代、武士時代、平民時代來取代古代、中世、近世等時代區分,試圖將古典文學放在「思想發展史」這個具普遍性的基準上來分析個別的作品。早川万年認為津田原即無意致力解讀古典文獻本身,其是以「國民」思想的發展為大前提,來評判典籍在思想發展史中的所占位置而已。津田的「記紀研究」著重的是在國民文化發展過程中,上代人的思想與記紀的關係;津田的論語研究(即《論語與孔子思想》一書)並非致力於解讀《論語》本身,而是在考察孔子其人與《論語》這本編纂書的關係為何,以此探討《論語》在中國思想史上的位置。因此,「津田史學」的實質內涵不可否認自有其侷限。
「津田史學」的侷限性亦與其歷史認知有關。津田研究的根本軸心是其個人對日本國民文化及思想發展「歷史」的絕對信心,以此作為史料批判的基礎,因此其考察結果多難以擺脫主觀認定之弊,無法真正地視史料典籍為「客觀對象」。這樣的歷史認知也如實反映在津田的中國思想研究中。中國學者劉萍在〈異色的道家觀-津田左右吉的道家批判研究〉(《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言語文學篇,第23號,二○○三年)一文即明白指出,津田立足於文本的「原典批判」,乃於文獻的精密分析裡闡述批判主義的文化理念,而在這批判主義背後支撐的,不乏明治維新以來至近代日本知識份子胸中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情懷。無論對日本的記紀文化,或對中國儒道思想,津田都試圖以近代科學的目光加以重新審視,力求做出超越近代日本國學家及漢學家們的闡釋。然而,其汲汲以求的,是要建立一個獨屬於日本民族自身的日本文化形象。在這個過程中,津田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在具有理性價值的背後,卻往往表現出對中國文化的深度冷漠與蔑視。
一般認為津田是以西洋文化(其謂之「世界文化」)為尺度來審視中國,視中國文化為停滯不前的文化;另一方面則透過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兩者的區別和分割,闡明突顯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是以津田的中國學實質上不免帶有輕蔑的味道。不過,溝口雄三則在〈津田的中國學與今後的中國學〉(〈津田シナ学とこれからの中国学〉)《作為方法的中國》(《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都: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九年)一文中指出,津田真正關心的是如何將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區隔開來,其儒教研究也是由此問題意識而生,因此在津田眼中,儒教始終是中國的儒教,其儒教研究旨在闡明儒教裡所反映的中國特性,可說是徹頭徹尾的中國儒教學。溝口雄三認為津田的中國學不僅止於事象羅列、表層皮相上的比較而已,且深入至原理性問題的發掘,而其所發掘出的原理性問題正當與否,不應與蔑視中國的價值判斷混為一談。長久以來,學者往往以津田自身名言——「被世界文化遺棄」的中國這種說法來概述津田的中國學,將其中國研究與中國蔑視、或忽視中國的獨特性等負面評價畫上等號,然而這些批判實與當代社會世相的「要求」、「制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以今後應該要有意識地脫却所處時代社會的制約,重新回到原理本身、原理的普遍性問題,再次審視津田的中國學。
一如溝上瑛在其文〈津田左右吉〉《東洋學的系譜》(《東洋学の系譜》)(東京都:大修館書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中提及,即便津田的研究與著作是應用西洋的史料批判方法,以日本的尊皇思想為基礎所建構出來的,但我們並不應就此輕易斷定他對中國或朝鮮有著民族歧視,若忽略了那超越人與人之間的信賴感,將會看錯津田的真正樣貌。《津田左右吉全集》補卷所收的大多數書信,可窺見其與朝鮮人門生深厚的信賴關係,這些將有助於修正過去一般對津田其人與學的看法。
無論是日本的「記紀研究」或中國古典批判,「津田史學」的主體是透過文獻史料的校勘與再認識,探討從這些史料中有跡可尋的「思想」。津田的研究主要是透過文獻史料來考察思想或歷史的演變過程,而其關注的更是隱藏在文字後面的個人或團體與現實生活的連結問題,因為文學、思想或哲學與生活本是密不可分的。津田思想史的意義在於津田並不單純地將思想視為與生活同體,而是肯定思想乃奠基於生活的同時也反省生活本身,是為一種表象,必須有意識地去追求。津田史學也因此獨樹一格,與過去的思想史研究有著一線之隔。
前言
《論語》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是記載著所謂的孔子言談,而此書是如何形成的呢?自古以來,學者們就這一點進行了諸多論述;到了近年,隨著對此問題的深究,大家也漸漸開始思考,在這本書所記載的孔子言談中,不乏讓人懷疑是否確為孔子所言的可疑記事。這個問題並不容易解決,但為了了解儒教的歷史,也為了究明被儒教尊為宗師的孔子之思想,此一問題極其重要,必須盡可能地去了解、釐清。筆者也將此視之為是與中國思想史相關的諸多問題點之一,從很久以前開始,一有機會便思索、考察此一問題,因此現今彙整個人研究,書寫成冊。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春,在東洋文庫所舉辦的東洋學講座上,筆者曾以「論語形成的過程」為題演講,此乃執筆的契機。
筆者企圖探究的根本問題是孔子的思想為何?孔子教導弟子們何事?以及孔子思想如何被後世的儒家之學所承襲、如何被改變?換句話說,就是孔子的思想於儒家思想發展史上是如何運作、發揮作用的這個問題。而在思考這些問題之際,《論語》中記載是為孔言的章句是否果真能夠照單全收、全盤相信,筆者則持保留、疑慮的態度,並以為其中尚有假借孔子之名來闡述後世儒家思想的記事,因此,這些記載自然便成了問題。而在探討這個課題時,「《論語》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也就隨之產生。所以《論語》形成的過程,對筆者而言,其實是衍生出來的課題。因此,本書不僅是處理《論語》作為一本書籍的相關問題,同時,還要考察《論語》包含了怎樣的思想?其與孔子思想的關係為何?到底為何又能夠由其得知孔子的思想?而這思想又是什麼呢?這種孔子思想與孔子以後的儒家思想之間又有著什麼樣的關係?等等問題。本書第五篇便是為此而寫的,一言蔽之,第五篇就是追溯考察從孔子至西漢時代儒家思想發展的過程、脈絡。就孔子的思想而言,因為時勢變遷與思想的普遍發展,孔子思想並未照原貌傳於世間;就之後的儒家而言,他們一邊祖述孔子思想,一邊不斷地添加新的色彩於其上,使其轉化成新的形態,因而促使了以孔子為宗師的儒家在思想上的發展。即便是在《論語》中,在某種程度上多少也反映出這樣的情況,這一點可藉由分析《論語》的內容而得知。
關於古代儒教發展的樣態,筆者已於二十年餘前的舊作〈儒教成立史的一側面〉(〈儒教成立史の一側面〉)《史學雜誌》三十六卷六、九、一一號(後收錄於《儒教的研究》﹝《儒教の研究》﹞一書),提出儒教的發達主要乃出於時勢變遷和儒者態度所致。現今看來,這篇文章裡有許多非訂正不可之處,而其中論及《論語》的諸點,則自然由本書來加以更正。不過,大致說來,筆者以為該篇文章中的論述並無太大錯誤,因此,待適當時機到來後,會再將前引文章和其他考察中國思想的諸篇論文一併以類似論文集的形式編撰後成書,發行於世。
筆者從以前便努力盡可能地少用中國的文字,所以在本書執筆時亦是以同樣的方式進行,但因為這樣的寫法還不夠成熟,多少不免存有使用中國文字和不使用中國文字的情況並行、不協調的情形發生。另外,筆者以為凡是日本的專有名詞應全都以假名書寫,是以本書亦如是行之。
在學術性書籍出版時機不佳、條件甚繁的今日,本書能公諸於世,多虧岩波書店的好意。然而,書店負責人岩波茂雄先生卻在筆者閱畢初次校稿之際,出乎意料地溘然與世長辭。長久以來,筆者與岩波先生不僅只是出版者和作者之間的關係,吾等友情深厚甚為親近,筆者心中悲痛筆墨難盡,而想到在日本文化事業上沒有比這更令人惋惜的事,更是痛心。雖然場合似乎不太適宜,請容許筆者在此特別誌記這件事以表達哀悼之意。另外,感謝該出版社的粟田賢三(アワタケンゾウ)先生與布川角左衛門(ヌノカハカクザエモン)先生兩位,在本書的出版上給了筆者許多照顧;西島(ニシジマクスヲ)先生受筆者拜託接下了校稿的工作;以及岡本(オカモトサムロウ)先生和松嶋(マツシマエイイチ)先生兩位友人的大力相助之下,書末得以加上索引。對以上諸位的協助,致上最誠摯的謝意。
第一篇 世間流傳的孔子言談
在許多各式各樣的書籍中都可見孔子所說的話,然而,仔細閱讀、相互比較這些所謂的孔子言談,或和其他書本所引各類辭句互相對照,則不難發現其中可疑者不少。事實上,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很有問題的。因此,第一篇先暫時撇開《論語》,舉例討論這些有疑慮的孔子言說。首先我想從西漢時代書籍中舉例來看。其原因有二:其一,因所謂的孔子言談其大多數記載於西漢書籍中。其二則是,與現今所傳《論語》幾乎完全相同的《論語》文本為學者間所知曉,約略是在西漢初期以後的事,所以,釐清西漢時期成立的各種書籍是如何記載所謂的孔子言談,又是如何地囊括、納含了可疑的孔子之言於其中等問題,這在思考《論語》的孔子言談到底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孔子所論述的這個問題,將有莫大裨益。(關於與現傳《論語》幾乎完全相同的《論語》文本是在西漢初期時為人所知曉一事,將於後詳述。)
第一章 與論語無關的孔子言談
一 西漢時代書籍之所見
談到所謂的孔子言談,首先注意到的,是從前代流傳下來或於此時成立的書籍中,有並非出自孔子所言,卻被視為其言論的情況發生。例如,《荀子》〈樂論篇〉中,有一章節起訖於「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文,此章節在《禮記》〈鄉飲酒義篇〉裡則被冠上了「孔子曰」三字,成了孔子所言。而《荀子》〈勸學篇〉「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以下數句,在《大戴禮記》〈勸學篇〉裡亦被視作孔子之言。另外,《淮南子》〈天文訓〉裡「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至「陽施陰化」之章節,在《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中,則成了曾子從孔子那兒聽聞而來的言辭。此外,《禮記》〈曲禮篇〉「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一文,於〈坊記篇〉中則加上了「子云」二字;而〈經解篇〉中敘述婚姻、鄉飲酒、喪祭、聘覲等禮之式微的章句,在《大戴禮記》〈禮察篇〉中則被當作是孔子的話。(〈經解篇〉雖同為西漢時代書籍,應較〈禮察篇〉稍早完成。)再者,在《穀梁傳》〈定公十年〉提及頰谷之會時評論孔子行為的記載裡,可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一文,然而此文在《史記》中,卻記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並視之為孔子所言。以上所舉數例中,《荀子》〈樂論篇〉的上述引用句裡有個「吾」字,即意味著某人所言,而其後又以「故曰」再次陳述同一辭句,由此或許可推測此句是從其他文本中擷取而來,但即便如此,也無法斷定此「吾」即為孔子,因為《荀子》中只要有引述孔子言說之處,必定會註明「孔子曰」三字,但此處卻不見此一標示。不僅如此,起訖於「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一文之全體章句,很明顯地是屬於荀子思想。所以,《禮記》〈鄉飲酒義篇〉是把非孔子所言當作為孔子言談而記載。(在〈漢儒著述的方法〉﹝〈漢儒の述作のしかた〉﹞中亦見此章節的相關討論,該論述必須重新檢討,應以此處論述為是。)在此順道一提,東漢的《白虎通》〈禮樂篇〉裡,則把《荀子》〈樂論篇〉「樂在宗廟之中」云云一文,作「子曰」而記。上述《大戴禮記》擷取〈勸學篇〉一文中,除了一兩個文字上的差異之外並無特別可議之處,而此文中也用了「吾」字,可視為荀子自己所說的話,應無大礙。另外,上述〈天文訓〉詞句和〈曾子天圓篇〉在文字上稍有出入,也造成意思上的些許差異,但很明顯地,後者是擷取前者而來的。「天道曰圓,地道曰方」至「陽施陰化」之章節內容與〈天文訓〉內容相符,思想也是屬於西漢時代的。(《大戴禮記》〈曾子天圓篇〉中並無註明孔子言談止於何句,同篇中亦可見擷取〈天文訓〉之詞句,或將其加以發揮之處,或許這些也都被囊括作為孔言。)再者,〈坊記篇〉中於「取妻,不取同姓」後添加了「以厚別也」一文,此句在〈曲禮篇〉裡原為「取妻,不取同姓」之前文,用以總結文句,〈坊記篇〉卻錯植了位置。關於〈坊記篇〉中「子曰」所指何人,將於後詳論之。上述〈經解篇〉和〈禮察篇〉在文字上雖有少許出入,但整體來說,詞句同出一轍是無庸置疑的。此外,關於《穀梁傳》和《史記》的關係,則在《左傳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篇第五章中有所詳述。
以上數例,皆為後來完成的書籍假托孔子所言,其原出處是可考的。而來源已不可考,卻被當作孔子言談的例子也不少。譬如,《史記》〈平津侯(公孫弘)傳〉中以「臣聞」所載的五「通道」和三「通德」,在〈中庸篇〉裡則記作孔子之言,這應該是〈中庸篇〉引用其他書籍所載而致,但現今已無從考證。然既以「臣聞」敘述,就意味著其言出自於某書,但是否一字不漏地按原文抄寫則無從而知。除了幾個文字上的出入之外,〈中庸篇〉裡的詞句和公孫弘上書大致相同,抑或是〈中庸篇〉逕自擷取了《史記》公孫弘上書的內容歟。《史記》中的「通」字在〈中庸篇〉裡作「達」;五「通道」中的「兄弟」在〈中庸篇〉裡則為「朋友」,〈中庸篇〉將「兄弟」改為「朋友」應是為了符合孟子的五倫。雖然〈中庸篇〉裡此章句是否作孔子所言記載並不十分明確,但至其前文為止明白揭示為孔子之言,且其後「生知學知困知」亦為孔子所言,由此可推斷此章句應是作為孔子言談而論。又譬如,《大戴禮記》〈主言篇〉裡有孔子向曾子講述「三至」的章節,謂「三至」為「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文亦疑似將他書文本挪作孔言而用之例。如此斷定是因為此句分釋「三至」者為三樣不同之物,文風屬道家之說,與後接孔子言說在文風思想與表達方法上大相逕庭,僅說明手法雷同而已。上引「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一文後面,孔子詳述「三至」者,謂「昔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明王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天下之士說,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文思想與文風皆屬儒家,將「三至」相互聯結論述,並非在說明「三至」為何,明顯與前文間存有極大歧異。由此可推論「三至」本為既有之說,前述孔子所言實為〈主言篇〉作者所添作。至今雖難以查證「三至」之說源自何書,然由其道家文風可推論應是西漢時代所作。因西漢時期有許多類似之作。(有關孔子言談為添作之說,將於後面再述。)
論述至此,順道舉些前代書籍裡明確記載為他人言談,卻被當作孔子言說而載的事例。譬如,《孟子》〈離婁篇〉下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文,於《韓詩外傳》卷三中則視之為出自孔子所言。此文原為孟子論述舜與文王兩者之結語,而《韓詩外傳》則將該論述內容一字不漏抄入,並在上引結語文前加入了「孔子曰」三字。不過,與此同時亦可見將孔子所言視作他人言談之反例。譬如,《韓詩外傳》卷三中,對於宋人回應前來憑弔宋國大水的魯國使者之言,孔子有所評論,孔子此番評述在《左傳》〈莊公十一年〉記載中,則被改為臧文仲之言。然而像這樣相反的例子,並不多見。以上所舉之例,實為他人言談,卻被當作孔子言談而論,如後所述,這種事例不勝枚舉。
談到孔子言談,第二個注意到的是,在前代流傳下的孔子言談中加入新的語句,或其詞句全體被重新改寫的例子。譬如,《呂氏春秋》〈孝行覽孝行篇〉樂正子春言談中,曾子從孔子那兒所聞「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一語,在《禮記》〈祭義篇〉則載為「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中雖可見與〈祭義篇〉相同敘述,但其將「無人為大矣」作「人為大矣」,且無「不辱其身」。上述《禮記》〈祭義篇〉與《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兩篇記事相較之下,前半部為〈曾子大孝篇〉較為易懂,而後半部則從其字辭相疊的語法來看,應是〈祭義篇〉較為正確。此外,雖然在字句上略有不同,《呂氏春秋》裡不見「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等三句,在《禮記》《大戴禮記》卻可見其載,這就表示了有新思想的加入。又譬如,《禮記》〈檀弓篇〉孔子知其死期將近而向子貢所述一文中,可見「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一文,但〈孔子世家〉卻將此文載作「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上引《禮記》〈檀弓篇〉與〈孔子世家〉二文,總的來說,即便其文意大致相同,但在敘述方式所展現的態度上,兩者卻有相當大的隔閡。(《禮記》〈檀弓篇〉與〈孔子世家〉此處記事的整體氣氛皆有些許不同。)以上這些都是因為被重新改寫而使得文意上或態度上都與原來文本有所差異的例子。儘管在整體文意或態度上沒有太大差異,但言辭語彙等有所迥異的例子也不少。譬如:《荀子》〈宥坐篇〉和《韓詩外傳》卷三、以及《淮南子》〈道應訓〉中所見孔子談論關於宥坐之器的內容皆有所不同,即為一例。《韓詩外傳》卷五所載孔子和師襄子的對話,在〈孔子世家〉中亦可見,雖然意思大抵相同,但兩者各自有其文意上難以理解之處:《韓詩外傳》中將孔子所言從「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立即轉接至「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而在〈孔子世家〉裡則將「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視為師襄子所言,此處即見分歧。這應該是將原來存在於其他書籍中的語句,各自分別加以改寫後,再收錄於兩書所致。但存有原來的語句的書籍是怎麼樣的書呢?現今則無從知曉。總之,也會發生類似上述這種情況。(此處所舉之例,除首例之外,皆為敘述有關孔子生平故事中所出現的語句,而關於這樣的孔子故事之後會再另行考察、詳論之。)
了解以上所述第一與第二兩種情況的事例後,第三種情況──也就是有新創孔子言談之產生,亦應不足為奇。其主要包括了,從思想面上看來必定成立於西漢時代者,立論於道家風的思考和想法者,甚或是囊括了以上兩者,納含陰陽思想、好生思想者,自五行思想而生者,與五帝系譜相關者,和占星術相關者等等。成立於西漢時代並立論於道家思想者,譬如《荀子》〈哀公篇〉的大道說,《韓詩外傳》卷五中評論關雎之言,《禮記》〈禮運篇〉大道與大同說,〈哀公問篇〉「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一文,〈孔子閒居篇〉的三無說等等。納含陰陽思想者則有《大戴禮記》〈四代篇〉中論「德」與「刑」、〈孔子世家〉中所見關於趙簡子之批評等例。含好生思想者則可舉《荀子》〈哀公篇〉論古時帝王之政為例。自五行思想而生者,譬如《大戴禮記》〈虞戴德篇〉關於東郊儀禮之說。而與五帝系譜相關者,譬如《大戴禮記》〈五帝德篇〉。和占星術相關者,則有《左傳》〈哀公十二年〉關於「螽」之說明,《漢書》〈劉向傳〉元延年間上奏書所引關於桀紂之世等例。此外,從《易經》似乎是在西漢初期為儒家納入的這一點來看,《易經》〈繫辭傳〉〈文言傳〉中的孔子言說,應該也是同一時期創作出來的吧。(請參照〈易的研究〉﹝〈易の研究〉﹞。)而西漢末期至東漢初期成立的多數緯書,全作出自孔子一事,亦不容忽視。從緯書這類書籍的編纂成書來看,自然地可推論,偽託孔子所言而各依己意創出各種言詞輿論,應是西漢時代儒家普遍的習慣才是。因此,即便並非如上所舉數例般具特殊思想者,亦不能否認此時代書籍中具有新創偽作孔言存在之事實。《禮記》諸篇中可見孔子談論禮樂之言論,然從禮樂之說在儒家思想裡的歷史地位來看,這些孔子言談也大多是西漢時代所作的吧。(參看〈儒教的禮樂說〉﹝〈儒教の禮樂說〉﹞第六章。)正如〈曾子問篇〉問喪禮於老聃的章節,向老聃問禮,是唯有在這個時代才可能說得過的。向老聃問禮一事本為道家偽作,將孔子置於老子之下,企圖營造孔子欲受教於老子的形象,而儒家則將此道家偽說採納,反而在問禮於老子這點上,將老子給儒教化了。而這也是因為儒家多少接納了些道家思想,甚至在關於禮的說明上也加入了道家式的解釋,同時在另一方面,儒學則占有官學之位,比道家更為得勢所致。此外,如後所述,〈中庸篇〉關於作禮樂的言論,也是根據西漢時代儒家的思想主張而產生的。而〈經解篇〉中可見孔子談論六藝之教的本質及其所失,這肯定是將包含了《易》的六藝訂定為儒家教科以後所偽作的孔言。訂定六藝為教科則是西漢時代的事。(上述〈經解篇〉偽作孔言,似乎是將《淮南子》〈泰族訓〉其中一節改寫後的文句,若果真如此,亦可將此例列為第一種情況。論六藝之失,特別是,甚至連一般認為是由孔子親自所作的《春秋》也舉出其所失之處,與其視之為儒家言論,不如說是既認可儒家權威,且處於儒家圈外者的發言,較為妥當。從此處亦可想見,以《淮南子》〈泰族訓〉為其本源自有其意涵。)以上所舉不過是少數幾例,但足以窺知此時儒家的做法。由此可見,先前斷定「三至」的說明是〈主言篇〉作者所作,並無錯誤。《禮記》〈坊記篇〉〈表記篇〉〈緇衣篇〉僅羅列記敘孔子言談,這些也都是西漢時代的偽作。〈中庸篇〉中符合西漢時代天下一統情勢的記事,亦作孔子言談而載,詳情則待稍後再述。另外,西漢末期成立的《左傳》中所見孔言,也多是其書作者之偽作。(參照《左傳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篇第七章。)
以上分成三大類所舉之偽作孔言,為何多是出自西漢時期的書籍呢?其主要原因在於,若不偽作為孔言,其言說將失去權威性吧。《淮南子》〈脩務訓〉謂「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此言可一併作為參考。西漢末期《周官》《左傳》成書;《古文尚書》出土事件傳世;或者是新發現各式各樣所謂的古禮等,都錯綜參雜著同樣的情況。(參照〈周官的研究〉﹝〈周官の研究〉﹞《左傳的思想史的研究》〈西漢的儒教與陰陽說〉﹝〈漢代の儒教と陰陽説〉﹞〈儒教的禮樂説〉等論著。)不過,第二種情況所舉之例本為孔子所言,因此不在此範圍之內,但其中仍可見由前代傳下來的語詞染上新時代思想色彩,或者按個人的解釋而重新改寫的情況。其中,也有一些是不具特別理由而擅改語詞或說法的。中國的學者,特別是古代中國的學者,在引用古人所言或書籍中詞句時,並非忠實地抄寫其文字語彙,而是十分自由地予以改寫,這似乎是當時相當普遍的習慣。至少,當時的學者並不認為改寫是決不可為之事。同一本書會有許多不同版本出現,其中一個原因也是出於這種改寫的習慣。因為竹簡做成的書籍是很難處理的,而在竹簡尚未普及的年代,多是用背誦,或者靠記憶口傳的方式記錄,因而導致非意圖性改寫的情況也不少。中國學者所缺乏的,是對任何事物在思想上追求真實、尋求真相,進而傳達的這種心態。又或者,因為對學者來說,學問本身不過是現實中追求名利的道具,相對他者,學問的作用在於宣傳某種思想或主張。這些暫且不論,古人的話,事實上就這樣一點一點地以不同的語詞或說法流傳於世。於是,自然而然地,這些相異的語彙、說法所傳達之思想上的各種歧異與變化也不少。然而,這種習慣不僅只是重寫古人所說的話而已,也誘使了、或者說是助長了偽作的風氣。所謂的孔言,就是像這樣地,在西漢時期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地現世,愈後期其數量愈增。而同一孔言在不同書籍中會有些許詞彙或說法上的差異,這並非是故意重作的,應是在口耳相傳或謄寫繕抄時,不經意地改以其所聽聞習慣的語調記錄,甚而乘興將新的語詞加入,或因文章語氣而落掉原有語詞所致吧。因記憶有誤或抄寫時的誤植,其情況之多更自不待言了。
然而,這種情形也絕不是西漢時代以後才開始發生的。如下節所述,在所謂的先秦時代也有同樣的情況發生。
二、先秦時代書籍之所見
第一,非出自孔子所言但視作孔子言談而論者,首先可舉《荀子》〈樂論篇〉「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一文為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一文在《孝經》第七章中為孔子所說。(《孝經》應是《荀子》成書以後才完成的,參照〈儒教の實踐道德〉,第一章第二節。)另外,《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篇〉記載了大禹以德而服三苗的故事,關於此故事以「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一文記錄之。其中,「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一文在《孟子》〈公孫丑篇上〉則作「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並視之為孔言。在《呂氏春秋》上引文中,「故曰」後文是否納入孔子所言,並不明確。然而,即使是將其視為孔言而論,特意加以「故曰」兩字的這種寫法,正意味著此句所載並非出自孔子所說。又或者,「孔子聞之曰」和「故曰」在文章裡是處於同等地位,此處是將孔子言談和近似格言的語句並列而論也說不定。又,《呂氏春秋》一書是《孟子》之後所編纂而成的,是以該文應是從《孟子》以前成立的某書中抄寫而來的。因非出自孔子所言但偽作孔言而論者,例子不勝枚舉,由此亦可想見,《呂氏春秋》該文應非抄襲《孟子》而來。此外,「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一文,相傳為孔子論舜之言,但在《孟子》〈萬章篇上〉孟子記述此言為齊東野人之語,並非孔子所言;「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一文相傳為孔子所說,但《荀子》〈儒效篇〉中荀子卻否認該文出自孔子。暫且不論孟子和荀子的評論具有何種意義或價值,從兩者皆有所批評來看,可推測在孟荀之際,作為所謂的孔子言談而傳世者,已有不可信者。即便批評駁斥所謂的孔子言談並非真正出自孔子所言,聞之者亦不覺得有何怪也,由此更可見偽作孔言情況之一斑。《墨子》〈非儒篇下〉孔子論舜曰「此時天下圾乎」,此句與上引《孟子》所載言詞雖有所出入,仍作孔子所言。其是否就此認可了此乃自古流傳於世的說法呢?〈非儒篇〉成書雖為《孟子》之後,但此言不見得是引自《孟子》。《韓非子》〈忠孝篇〉亦可見認可上述言論為孔子所言,其後再予以詰難的敘述,然而,這只是為了責難孔子而援引《孟子》加以利用的例子而已。會說是援引《孟子》,是因為《韓非子》此記事後面所載孔言,與《孟子》於孔言之前以「語云」所記錄的文字意思相同,《韓非子》應是擷取此文連接於孔言之後。這也是並非出自孔子卻視作孔子言談而論之例。另外,《韓非子》所載孔子在談抄寫時做了語詞上的轉換,是為「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第二,則是改作孔子言談的事例。譬如:《孟子》〈公孫丑篇〉「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敎不倦也」與《呂氏春秋》〈孟夏紀尊師篇〉「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之例。上引《孟子》《呂氏春秋》記事,用或不用「聖」字文意相去甚遠,在說法上也有些許差異,很明顯地兩者之一是為原作孔言,其他的說法都是以其改說、加以換作而成的。從兩者成書的時代來看,一般或可視《孟子》的記事為原作孔言,然而,將孔子視作聖人來看是很特殊的一種思想,乃孔子觀已經發展成熟階段的產物,因此這或也正意味著《呂氏春秋》所引孔言確為原本,不是嗎?又譬如,《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耳」之孔言,是將《孟子》〈離婁篇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記事與〈滕文公篇下〉「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一文兩者相接,再加以改寫而成的。(參看《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二篇第七章。)筆者以為《公羊傳》內容中最古的記事,大抵為戰國末期所寫,儘管上引《公羊傳》記事不知是何時完成,即便把撰寫年代向前推的早些,亦應是在戰國末期成立才是。(參看《左傳的思想史研究》第一篇第二章。)
第三,則是新作孔子言談的產生。從思想上來看,討論堯舜者、論述《春秋》一書者,皆為新作的孔子言談。堯舜的故事、《春秋》一書皆是在孔子之後,大概在進入戰國時代以後才現世的。(參看〈儒教成立史的一側面〉﹝〈儒教成立史の一側面〉﹞二、《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二篇第六章、第四篇第二章。)談論所謂三代之政的《書經》諸篇、《詩經》〈雅頌篇〉等皆是孔子之後才成立的,所以可判定那些孔子論及《書經》《詩經》的言詞也都是後來新纂編作出來的才是。《書經》《詩經》的記事就之後再行討論,至少在孔子論及堯舜的故事及《春秋》一書等言說,十分確定是新作出來的。然而,這些新作孔言在《孟子》中就已經出現,可見這種新作孔言應是在《孟子》編撰成書以前早已撰寫成立了。孟子評定為齊東野人所言的記事乃論舜世之事,雖與孟子所評意義不同,但該記事並非出自孔子所言。而在孟子的時代,像這樣的記事常被當作孔子言談流傳於世。從這個例子來看,其他所謂的孔子言談裡也很難說不會有偽作的情況存在。《孟子》編撰成書之後,戰國時代末期漸漸現世的許多道家書籍被編入《莊子》一書,其中記載了許多所謂的孔子言談,然這些言談中闡述道家思想者應視為是道家所作,《莊子》記載孔子受教於老聃的故事,是將孔子給道家化了。不過,筆者以為道家會這麼做應該是受到了儒家裡有新作孔子言談的這種習慣影響所致。也就是說,一如道家偽作孔子言談亦不足為奇,即便是儒家也同樣有偽作孔子言談的情事。然而。與此同時,道家在行偽作孔言之際,儒家方面為了與其對抗,也另創了孔子言說吧。要一一具體舉例證明雖有困難,從戰國時代末期儒家與道家相互影響且互相抗衡的情況來看,筆者以為是可以如是推想的。如前所述,到了西漢時期儒家甚至出現了孔子向老聃問禮的這種記事,儒家的此種態度也可與此一倂考量。不只是孔子所言而已,這個時代本就有許多古人或視之為古人所言新創產生,甚至連神農、黃帝等人之言也多所現世,因此孔子言談也同樣有新作孔言的發生,亦絕非不可能之事。然而,這種偽作並不限於傳達道家、儒家的特殊思想之用,亦可見於只要是偽作為古代某人所言即可的情況。《韓非子》〈內儲說上〉將同一語句當作孔子和晏子所言記載,這是因為不論是作孔子或晏子之言,都不具特別意義,正顯示出其不過是當下浮現腦海之產物而已。《莊子》〈至樂篇〉出自孔子所言,在〈達生篇〉則為扁子的話,也是一個相同的例子。
然而,儒家中假托為孔子所言的一本特殊典籍,成書於戰國末期,此即為《孝經》。《孝經》中孔子曾向曾子闡述儒家道德思想最為重視的孝道。如上所述,《孝經》中可見引用《荀子》的記事,由此可推知《孝經》乃此時撰寫成立的,而將「孝」與「忠」相互對立、置道德之基礎於天地等儒家之說,似乎亦是此時首次被提出來的。在論述某事時,斷章取義地引用《詩經》《書經》等手法從更早之前就開始了,而將其擴展套用於孔子所言者,《孝經》恐怕是濫觴。若果真如此,這也顯示了《孝經》是在偽作習慣相當普及以後成立之書,也證實了《孝經》確實撰寫於如上所述之戰國末期。儒家對某事物的思想以較有組織的方式敘述、撰寫成一本書籍,並將其內容全視為孔子所言者,現存典籍中以《孝經》為始祖,而像這樣偽作孔言情況也於焉產生。簡而言之,先秦時代已偽作創出各式各樣的孔子言談。
一般來說,先秦時代偽作孔言的產生,其緣由與上述西漢時代的情況相若。《淮南子》〈脩務訓〉所述內容,與知識分子欲為君主所用、欲得地位利祿而汲汲營營的這個時代最為相應。隨著此時儒家之教正日漸形成一門學派之際,其宗師孔子則被視為人上之人、甚或某種意義上的超人;另一方面,與儒家相對立的各種學派相繼出現,各自以其不同立場與態度來看待、處理孔子,因此孔子所言也就在上述情況下被大量竄改甚或偽作了。本來這些情況應是這個時代較為後期產生的,但較此時之前,儒家本身重大而根本的問題在於,隨著從孔子到孟子這段期間時勢的變化──即所謂戰國時代的展開,視孔子為宗師的儒家,其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化,必須將新的儒家思想以孔子言說來表現才行。因此,新的孔子言談就這麼被偽作出來了。以上所述有關堯舜的故事、《春秋》之成書,以及關於這些的所謂孔子言談之現世等,皆為一例。即使沒有那些外在因素,隨著儒家思想本身內部發展,在教義上產生新方向時,則將此新方向以宗師孔子所言顯現於世,因此而促成了偽作孔言誕生的情況也不少,《孝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在此僅大致說明竄改及偽作孔子言談的情形,對於儒家思想變化,則另循機會再作討論。
另外,不具特殊意涵,亦非特意竄改,單是文字上的些許誤寫錯植,這種情況也是有的,也得考量。這也跟上述西漢時代的情況相同。譬如,《呂氏春秋》〈慎行論察傳篇〉談到子夏時「己亥」一詞誤寫為「三豕」;且與孔子相關記事中,「一足」一詞可作兩種解釋。(「一足」的記事亦見於《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前者的情形極為常見,但像後者那樣,把詞彙語意變改為完全不同意思的情況,也是會發生的。
三、孔子故事裡的孔子言談
所謂的孔子言談,可分為兩種。一是單就孔子所言而留下的記錄,另一則是在孔子軼聞故事中所載的言談。目前為止本書所談論的多指前者而言,但也有後者的例子。然而,孔子軼聞故事內容也會有所演變、發展,在探討這類孔子言談時,則也必須一併考察故事本身。以下即針對孔子軼事如何變化、如何發生等問題,舉例二三,作個概括的考察。
論孔子軼事,必須從兩點來探討,一是既有的故事其內容日漸有所轉變,一是故事本身就是新創出來的。暫且不談《論語》,現存記載孔子軼事最古的書籍,就是《孟子》,但記錄並不多,亦非詳實。然而,到了戰國時代末期,有許多孔子的軼聞故事出現,並且敘述得相當詳盡,姑且不論《莊子》諸篇中特意加入、別具意涵的孔子軼事,《呂氏春秋》中可見許多諸如此類的故事,《韓非子》裡也是。到了西漢時代,此類書籍數量愈漸增加,自不待言。然而,雖然要釐清現傳數本書籍裡所記載的某故事,在不同書籍間其內容變化的過程是很容易的,但要知道此故事何時開始流傳於世,則相當困難。因為即便是現存書籍所載的故事,應該也有抄自佚書的,或是以其為本而重新改作的內容。因此,在上述兩點中,關於後者部分,有許多情況是無法確實掌握的。
談到孔子軼聞,首先浮現腦海的就是「陳蔡之厄」,而這個故事在《孟子》〈盡心篇下〉已有所載,可見是在〈盡心篇〉前就流傳於世。此故事或以實際情況為依據,靠著某種程度的口耳相傳所生。然而,《孟子》並無該故事內容的相關記載,戰國末期以後的書籍則對此多所論述。(《論語》亦可見「陳蔡之厄」的故事,但此處暫且不論。此處乃是研究與《論語》章句無關的孔子故事,而「陳蔡之厄」這則故事,一、在考察孔子故事變遷的過程、脈絡上恰好合適,二、且大致可在不牽扯《論語》記事內容的情況下探討,因為這兩點,故於此處舉此例來討論。)這則故事在經過相當的發展後,出現在《呂氏春秋》〈孝行覽慎人篇〉與《莊子》〈讓王篇〉中。內容是說孔子雖陷於困境,連食物都沒有了,仍弦歌鼓琴。子路和子貢揣摩不出孔子之意,子路便去詢問孔子,孔子於是闡述「窮達」之意,言「窮」乃窮於「道」,「達」者達於「道」,自己並不「窮」,而後再度撫琴,子路便執干而舞;子貢則說古時得「道」者不管是「窮」或「達」,快樂是一樣的。在這則故事裡顏回也有出場,但僅是露個臉罷了。《呂氏春秋》與《莊子》記載的是一模一樣的故事,文字上也無甚特殊差異,只是《莊子》的記事將「達」記作「通」。還有《呂氏春秋》裡,詢問孔子的人是子貢,這似是「子路」的誤植。這則故事因為在言孔子「窮」這件事,所以這個「窮」是取窮達(窮通)的「窮」之意、並由此展開者,而經常性地弦歌一事也有其意義在。(又,在《莊子》〈秋水篇〉裡有孔子等人於匡地被圍時,孔子弦歌鼓琴,並向納悶於此的子路解說「窮通」乃「命」也「時」也的故事。這是在相同的情況下闡述相同的道理,或許是將在陳蔡發生的故事當作是在匡地發生的事也不一定。)然而,《荀子》〈宥坐篇〉所見故事裡,子路向孔子請教的問題,是累德積義的夫子為何未得福卻遭禍,對此孔子舉古時正直者未受重用反遭禍害的前例,教導子路「賢」與「不肖」乃「材」也,「遇」與「不遇」卻是「時」也的道理,因此應博學修身以待時機。其中沒有記載弦歌之事,顏回和子貢也沒有現身。與《呂氏春秋》等的記事相較來看,《荀子》言「遇、不遇」和言「窮達」是出自同樣的意義,但《荀子》該記事乃是以修身為主軸,與《呂氏春秋》等書重點放在不因窮達而改其樂的這一點,其間的心境不同。與這段〈宥坐篇〉的記載意義相同的故事出現於《韓詩外傳》卷七,辭句也有某部分相同,僅孔子所言中出現的古人之名與其事蹟大幅增加這點,與〈宥坐篇〉的記事相異。接著,之後的《說苑》〈雜言篇〉則有兩則故事,其一為承襲〈宥坐篇〉和《韓詩外傳》的記載;另一則是孔子吟歌奏樂,子路因而先問此為「禮」否,再循問其是否為「時」,之後再添寫,待化險為夷後,子貢對孔子說:弟子們皆言因為追隨夫子而遭難。這確是改寫《呂氏春秋》與《莊子》的記事而來,子貢的出場亦應是同理,而孔子向子路和子貢論述的言談中,則有取自〈宥坐篇〉之處。另外,成書年代處於〈宥坐篇〉、《韓詩外傳》與《說苑》之間的〈孔子世家〉裡,則有這樣的故事:孔子即使陷入困境也未停止講頌弦歌,子路因此憤而質問孔子君子亦有窮乎?孔子對此則說君子固窮。子貢亦怒形於色地與孔子進行問答。孔子見弟子們似乎心有不滿,便逐一喚來子路、子貢與顏回,引《詩經》之句,問曰「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並對各人的答案一一發表意見,最後聽聞顏回的答案時欣然而笑。〈孔子世家〉讓子路、子貢和顏回發揮作用的這一點,是承繼《呂氏春秋》與《莊子》的記事;孔子就子路的回答所發之言論裡,雖也有取材自〈宥坐篇〉與《韓詩外傳》的記事之處,但故事本身卻是截然不同。
以上所舉是載錄「陳蔡之厄」的主要幾則記事,不論是哪一則記事,應該都是從一個故事,以其為本所變化出來的各種型態。原本的故事是怎麼樣的內容,雖不得而知,但將這幾則故事比較對照來看,就孔子言談中所見思想與弟子中只有子路發揮作用、戲分較大的這一點來看,可判斷〈宥坐篇〉的記事似錄有原作故事的痕跡在。然而即便如此,從原作的角度來看,〈宥坐篇〉這則記事似是加了相當多的修飾。孔子講述給子路聽的部分有兩段,「孔子曰」這三個字則出現了兩次,這大抵是因為引用了其他書籍所載此則故事中的孔子言說,再將其加在原作故事上而來的吧。《呂氏春秋》與《莊子》的記述,不管是就賦予弦歌意義、或孔子言談裡所顯現之思想、還是子貢的活躍和顏回的出現這一點看來,與〈宥坐篇〉記事相較之下,都與原作來得相距甚遠。但〈宥坐篇〉的撰寫應是在西漢時代初期,較《呂氏春秋》與《莊子》二書為晚,因此可以推測,在這兩本書成書之前,就已有〈宥坐篇〉引以為典據的原作故事存在了,而此二書所載記事乃自原作故事變化而來的。不僅如此,《呂氏春秋》裡的這則故事,可能是自從前就有的某書中抄寫而來,或是將該書的記載內容修飾過後的結果,應是此兩種情況其中之一,因此,若《呂氏春秋》成書之際就已有這樣的原作故事,那麼這個故事應是從很久以前流傳下來的吧。(若將前面提及的《莊子》〈秋水篇〉裡孔子於匡地的故事,視為是將在陳蔡的故事套進在匡地故事的結果,那麼其原作的陳蔡故事裡則子貢未有表現、顏回亦未露臉,似乎是較《呂氏春秋》所載更為單純的故事。說不定只有孔子於陳蔡弦歌,並向納悶於此的子路解說窮通這一部分的故事是之前就有,而《呂氏春秋》的記述是將其加以修飾後的故事。前面筆者所提「從前就有的某書」裡,早已載有這樣的故事。)《莊子》〈讓王篇〉似乎是較《呂氏春秋》為晚的書籍,因此將其中所見視之為抄錄自《呂氏春秋》,並無不妥(參照《道家の思想とその展開》第一篇第二章)。簡而言之,從以上所舉數則故事,可推知以下諸點,戰國時代中期之後的某個時期,敘述孔子在陳蔡受難的故事形成,之後便隨著時間變遷而有各式各樣的變化。其中有承襲原作故事的思想和型態較多者,〈宥坐篇〉的記載就屬於這個系統,而之後便由《韓詩外傳》的記事所繼承。不過〈宥坐篇〉該則記事裡似乎至少取材自同一系統的兩則故事。另外,與上述系統相異的故事則由《呂氏春秋》所取用,亦為《莊子》所繼承。這兩種系統的故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書籍裡,以各種不同比例混合在一起使用。不過,因為《史記》〈孔子世家〉的記述,就故事整體而言並不隸屬於這兩個系統,所以其似乎是在〈孔子世家〉新出現的故事(關於此點容後再述)。因此,像這樣地不斷變化或新出現的數則孔子故事中所記載的孔子言談,各自形成內容迥異的言說,此自不待言,而其間的差異,亦可藉前面所述得知一二。
另外,《莊子》〈山木篇〉可見孔子困於陳蔡時,大公任慰問孔子,以及孔子與顏回論歌的兩個故事。前者是藉大公任之口論述道家思想,孔子聽其言後曰「善哉」;後者則是孔子自身陳述道家言論。以上兩則故事,前者與其說是孔子困於陳蔡的故事,不如說是因相傳孔子曾有「陳蔡之厄」,而添附加上道家思想的產物較為妥當。然而後者故事中,孔子高歌並與顏回對話這兩點,則與先前所述《呂氏春秋》的記事有關。《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記載了顏回為勸孔子用餐,一面炊飯一面將半生的食物從爐上抓起而食的故事,以及孔子對此的論述,而《墨子》〈非儒篇〉則載錄孔子不問子路為何有豬肉,即將其所烹調的豬肉吃下肚的故事,其後並敘述了孔子對此事的看法。上述兩者皆是從沒有糧食這點所作的故事。雖然以上兩則故事將孔子與其弟子描述得相當不好,但從戰國時代末期已有如此的故事成立來看,可推知,筆者前述所謂的原作故事,應是從更早以前就已經流傳於世,與此同時,故事中的孔子言談也被改寫成各式各樣的內容才是。
「陳蔡之厄」,雖不過是諸多孔子故事中的一個而已,但孔子故事內容流轉演變的情況,則從此例可窺見一斑。孔子窮於陳蔡之事大抵是基於實際經歷、以此為本的某種口傳故事,(實難確認真偽,)即便是此故事之原形,恐怕也是之後再作的。因為若原作故事中有孔子與子路的問答,且其如《荀子》〈宥坐篇〉所傳載般的內容,那麼這不過僅是對於所謂不遇於時者的,一種普遍的、公式性說法之展現罷了。然而,諸多孔子故事中,是出自其實際經歷者亦不多,《穀梁傳》《史記》《左傳》所載頰谷之會裡的孔子故事即為一例(參看《左傳の思想史的研究》第二篇第五章。)特別是《左傳》所載孔子言談,是奠基於《左傳》一書的精神,由其書作者所偽作的(參看《左傳的思想史研究》第二篇第五章。)所傳獲麟的故事亦不應視作孔子實際的經歷,此自不待言,而故事本身似乎也並非自古所傳(參看《左傳的思想史的研究》第四篇第二章。)又譬如,〈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在陳國聽聞魯有火災時,曾說燒掉的應該是桓公和釐公的廟吧,而結果真是如此,此故事亦載於《左傳》〈哀公三年〉,但《說苑》〈權謀篇〉中則是記載孔子與齊景公對談時聽到周的廟燒掉的消息,便說那應該是釐王的廟吧,而情況果真如此。《說苑》所載明顯地是改寫〈孔子世家〉的記事,但〈孔子世家〉所載亦並非事實。然這又是從何時開始流傳的故事,則不得而知。此類之例不計其數,筆者在此僅舉一例與弟子相關的故事說明之。在《詩經》〈素冠篇〉毛傳中可見子夏、閔子騫各守喪三年完畢後彈琴的故事,一倂記載了孔子對其之評論、子路對孔評之疑惑以及孔子對此所作的回答、說明。此記事應視為是《禮記》〈檀弓篇〉在相同狀況下論述子夏與子張的記事之改作,特別是子夏的部份,其內容與前者相反。雖不清楚為何要改作,但從《淮南子》〈繆稱訓〉中與此相同的故事中僅見閔子騫這點來看,應是擷取此話、將其與子夏的故事相連結而寫成的吧。(現傳〈繆稱訓〉中不見閔子騫的故事,但注釋中有載,此處如王引之所述,原應為文本所載才是。)此外,《禮記》〈檀弓篇〉並無孔子所評,亦不見子路之問及孔子說明。而不論是孔子的說明也好,或者子夏與閔子騫、子夏與子張各自所述的內容也罷,皆與《禮記》〈喪服四制篇〉所載內容相同,唯其不以出自孔子或其弟子言談記之。(另外,〈繆稱訓〉雖也有孔評,但其說法迥異。然在有所評論此點來看,或許《詩經》〈素冠篇〉毛傳是學自〈繆稱訓〉也不一定。從以上的諸例,以及故事本身並非是陳述事實的這兩點來看,可推知這個故事應是根據西漢時代儒家所盛行的〈禮〉的思想而創作出來的。〈檀弓篇〉中孔子祥後彈琴的故事,亦與此同。(關於這些故事,後面應會有機會再述。)
孔子故事中,有些是由任何人來看都清楚知道是基於道家思想僞作出來的,譬如《莊子》所載的孔子軼事。而那些基於儒家思想所作的孔子故事,則因為孔子是儒家宗師,儒家思想即是孔子思想,或者自古相傳儒家思想為孔子所實踐等因素所致,往往很難讓人想到有可能是偽作的。然而,儒家思想本身也有歷史性的轉變與發展,孔子思想與其後的儒家思想迥異,若考慮到其後之思想因時代而各有所異,那麼藉由釐清這些故事中所展現出來的思想內容,來確認其是否是為偽作,也不一定是難事。若確為偽作,那麼也應多少可以推敲出是何時偽作出來的。偽作故事中的孔子言談亦是如此。若道家偽作了許多孔子故事,那麼很自然地,也必須考慮到儒家應該也會有僞作的情況吧。而對那些缺乏特殊思想性內容的記事,要從思想上推論其產生年代本非易事。這種情況,只有從故事最先出現的書籍成立時間來推知,但很多時候這些書籍並不傳於後世,是以由此點亦難以確定故事成立的年代。而在這類故事中的孔子言談,情況亦然。
網羅所有與孔子相關的故事並加以考察,是確立孔子傳記的必須工作,但這並非本文主要目的,是以此節僅舉二、三例,來探討所謂的孔子言談在孔子故事裡、或者與孔子故事一起被新創、重作的過程。